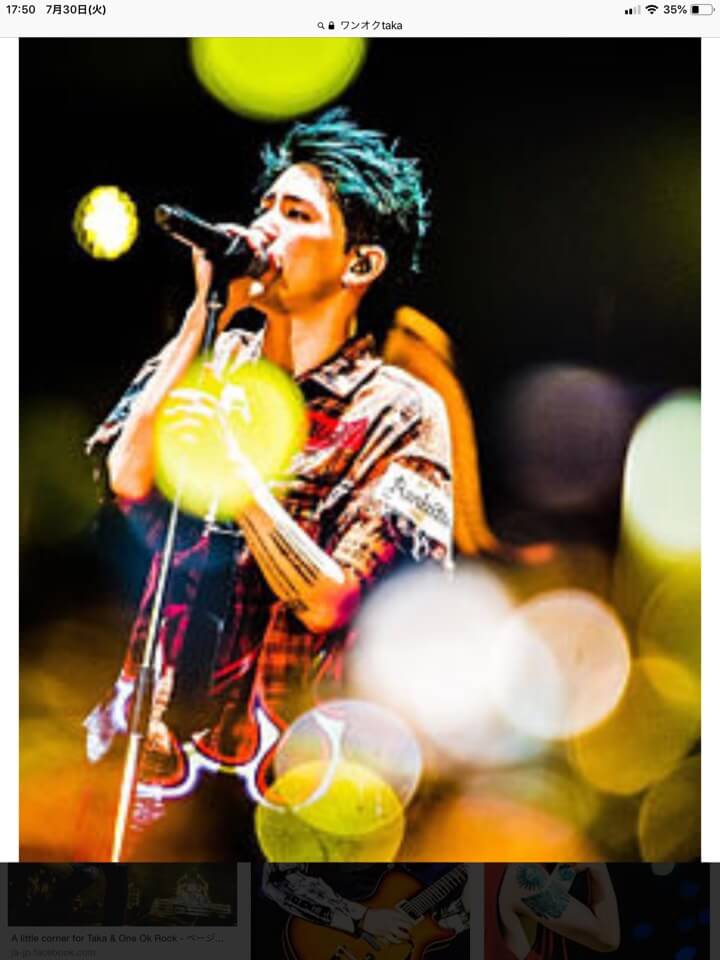描写日出的散文
描写日出的散文(必读6篇)
在金沙湾,等待一场日出
文/卢雪儿
我们一行人到达金沙湾,是晚上十点半。下了车,一股暖风扑面而来。商业楼被五彩缤纷的灯光染亮,在夜里,散发着迷人的色泽。门口有许多复古气息的木桌木椅,桌上食物琳琅,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三两罐啤酒,这般生活,好生惬意。早在来时的路上,我们已然决定了今晚在这里,等待一场日出。
本该寂静的夜晚,却传来阵阵歌声,我们循着歌声走上前去,看到抱着吉他弹唱的盲人歌者。若是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是盲人,我无法想象这动人的歌声竟是出于这些见不到光亮的人,心里不由地萌生了几分敬意。低沉的声线似乎就是为夜晚而生,一首首民谣歌曲装点着迷蒙夜色,伴着海风,别有一番滋味。
我们此行是为了日出而来,却也怕睡过头,是早已做好了不睡觉的打算,颇有点武侠小说里各路英雄好汉混迹于江湖时的豪气。只可惜英雄好汉是煮酒论剑,谈天说地。而我们,却只有一副扑克牌,一部手机,几杯热巧克力,这样看来,豪气自然是没有,倒是有几分烟火气。我们在烧烤店面前的木桌上打牌,在打牌的欢笑声中过了许久,原先灯火通明的一家家店铺依次关门,街上的声音渐渐隐去,直至悄然无声。此刻的金沙湾陷入甜甜的酣睡,像睡在柔软襁褓中的婴儿。
我们在半夜两点一刻来到海边,准备在这里吹吹海风,等待日出。深夜的金沙湾温柔至极,海浪声像叹息般,海风轻轻吹起发梢,动作轻柔,打着转,淘气地钻进衣领。远处的灯火氤氲成一片绮丽的灯海,远在天边,却也像近在眼前。灯光闪闪,刹那的恍惚,会分不清眼前的光亮,究竟是灯光还是天上星。在这样静寂的夜里,微乎其微的情绪将此刻渲染得妙不可言。耳机里反复播放着张国荣的《春夏秋冬》,轻柔的旋律适合在这样温柔的夜晚反复听。"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在这样柔软得像一缕薄烟的夜晚,内心平静得经不起一点波澜,却也暗自希望,下次再来时,是跟着恋人一同前来。
在这样轻柔的曲调和温柔的海风里,同伴在身旁睡着,轻轻的呼吸声消散在海风中,我却久久未能入睡,不知怎的,有种难以名状的错觉,那便是害怕自己这一睡,醒来便会错过心心念念了许久的日出。我看着远处几盏迷离灯火,不知是我在看灯火,还是灯火在看我。时间随着海风的轻拂缓缓流逝,面前依旧是一片海,几盏灯,几缕风。
凌晨六点,金沙湾伸了个懒腰,天空一隅从墨黑变成了淡粉与柠檬黄交织成一片的唯美画面,像极了童话书里的插图。天快亮了,我们纷纷起身。黑夜与白天相间的间隙,天地间美得一塌糊涂。若是诗仙李白在此,定是能写出与"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相得益彰的唯美诗句来。天空一点点苏醒,远处露出了一角橘黄,我们欣喜万分,期待了一整个晚上的日出终于肯给我们几分薄面,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整个日出过程前后不过五分钟,若有若无的一点淡粉隐匿于远处的高楼后,逐渐将海面染成一抹像少女脸颊那般粉红的色彩。海面红波涌动,极尽温柔。一叶渔船误闯入眼前这幅绝美的画中,划船的动作轻柔,怕惊扰了漂浮在海面上的阳光。太阳渐渐升了起来,变成了一枚大大的荷包蛋。是一枚未煎熟的荷包蛋,蛋黄液流向四处,为海岸四周镀上了一抹金黄色。我们索性脱了鞋子,赤脚踩着海水。海水温热,撞上了我们的脚踝,又匆匆退去,怕被我们责备。海边的人多了起来。三两成群,或玩水,或玩沙子,热闹的很。
看完日出,我们的心愿也算是完成,寻思着到附近吃点早餐便沿路返回。我走了几步,惊觉背包似乎比昨晚来时沉重了不少。仔细思索了一会儿,突然恍然大悟,它装载了昨晚绝美的夜色和今早娇羞的日出,难怪这般沉甸甸,便觉得不奇怪了。
日出东海
文/贺晓林
家乡人爱看戏,就象吃踅面离不了猪油辣子。
为了一台戏,可以赶十几里地。中午饿了,一碗油烘烘的踅面,要不蹲在戏台角下啃个冷蒸馍,口袋里装几只辣椒或大蒜就着吃。看了午场,还不过瘾,干脆撂下地里农活坐在台下等着晚场戏开演。
那个年代朴实的庄稼人,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苦耕劳,在农闲时看上一台大戏,那种喜悦比过大年还高兴。爱看戏,更爱唱戏,而且绝对是在骨子里的爱了,所以,那个年代,村上也就有了各具情态的戏痴来。
我巷里有个喜娃,算得上是个戏痴,一提起戏,那可是发了疯的爱呀,可他就根本就不懂戏,嘴里总有哼不完的"滴溜当啷"子,唱一些他都弄不懂意思的几个字。
喜娃有个习惯,只要掂上农具出了老城门他就喊上了,还多得唱个旦角戏,《三滴血》里小旦的几句戏倒被他唱的有滋有味的:"未开言来珠泪落,叫声相公小哥哥……"他眼睛睁的圆圆的,脖子伸长长的,嗓子更是压的细细的,要是再跟上几个年轻的媳妇娃,他就越发地卖弄自己了,骚情、妞捏、夸张的面部表情不说,总还使个小动作,那屁股和那老腰身拧的呀!也分不清哪里是腰?哪里是胯?
"看看看,毛老汉了,一脸胡子毛,咋总还爱唱个昆角戏。"
"老怂就不正经,老咧还俏俏呢,锄地没劲,唱起戏来那沟子拧得生欢。"
不知谁家胆大的婆娘子在他那拧得正欢的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脚,却见他更加得意地连蹦带跳。其实他就只会唱这几句,一唱就是多少年,而且每次还都是那样的自我陶醉着。
巷头第一家,住着位近八十多岁的老人,年岁大了,村里没几个人知道他老人家的名讳了,他家辈分高,有叫他"海爷",也有叫"海姥爷"的。
一天,喜娃和邻居们又要下地了,出了老城门,就拐到海姥爷家的院墙下。
"喜娃,扯两嗓子吧,好几天都没听你叫唤咧,有点不习惯。"
"有啥新段子来一段,别老是小哥哥老哥哥的,有吗?"
喜娃也想卖牌一下,几天都没唱了,嗓子确实有点痒。
"好,就唱个么,前几天电视放了刘易平的《辕门》,我听了几句给你们唱唱。"
"我的娘听一言肝胆气坏
把儿父推营门要找头来
你的儿杨彦景三魂不在
忙跪倒八个子两个裙才
清早间只看到日出东海"
"喜娃呀!你唱的看到日啥海呢 ?"有人问喜娃。
"日出东海,太阳从东海升起呀"喜娃再解释说。
"日出东海?"
"哈!好一个日出东海"
"哈! 哈哈 !唱得美,好戏,你再敢唱一句?"
喜娃叔得意了,又来了句:"清早间,只看到日出东海哎嗨哎嗨吆……"
突然,只听得"哐"的一声,海姥爷家的大门重重的撞开了,还没等响声落稳,气冲牛斗的海姥爷已经跳出家门,他满脸通红,额头的青筋暴的老高,脚上蹬一只老布鞋,另一只却在手里提着,他一阵连跑带跳,嘴里骂着:"你个小崽娃,叫你怂唱" 顺势扔出手里的鞋。"啪" 的一声,一只老布鞋甩在喜娃叔的屁股上。
"叫你唱!叫你还唱!小猪崽娃子,你个猪夿哈的。"海姥爷不歇气的叫骂着。
"咋咧!咋咧!好爷哩,你老咋喋我哩?" 喜娃叔跳着、躲着,大家却笑着。
"你还看到‘日出东海’,我道看见日出你娘的脚,你个小猪崽娃子,你,你再唱一句看看。"
看着喜娃叔挨打,大家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眼看把几个年轻媳妇撂了肩上的农具,捂着已经笑疼了的肚皮"哈哈哈",怎么也停不下来了。 旁边的顺喜伯说了:"好喜娃哩,清早间直跪倒日落西海你咋唱成清早间只看到日出东海,跪到和看到,西海和东海就不是一回事么,人家海爷的大名就叫东海,你不挨打才怪呢。"
"我以为!看到太阳出东海哩,谁知道、他、他老人家叫东海呢。"
"记着,是直跪到日落西海,你再敢唱日出东海,看我不敲断你娃那狗腿。"海姥爷说着捡起他的老布鞋回了家,看得出他也并非是真生气。
海姥爷的大名叫"东海",可喜娃并不知道。从此,再没听到喜娃唱那句戏了,再若唱,也仍然是他唱不够的旦角戏:"未开言来珠泪落,叫声相公小哥哥……"
要是有机会来我村看看,没准还能听一段喜娃叔的唱腔呢,不过声不细了,屁股也不拧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七十开外的老人了。
日出桑间
文/常龙云
老屋后有洼大水田。无风时,水镜映照白云青天、绿树碧山、行人、飞禽和走兽。风吹大田,水光涟滟,漾乱一田物事。
春天,野草疯长,围了大田。养蚕人冬天用生石灰刷白树身的光秃秃的桑树,重披绿装,柔枝婀娜,嫩叶鲜亮。这时,大田不见水,秧苗铺翠,欣欣争向荣。
春天太丰茂了,没人在意大田边那株低矮小树。它混生桑间,枝若桑,叶若桑,大家都清楚它不是桑树。它的下部被野草遮没,看上去矮矮一丛,毫不显眼,卑贱又顽强生长着。清晨出门,见太阳升起在树梢,仿佛从树下爬上来的,或从树间走出来的,枝枝丫丫恰似众多的手,将它托举起,光照原野。
说它小树,是因为它永远是矮矮一丛,留在我记忆里。虽然它年年努力,春天生出众多枝丫,簇拥着向上,但生长出来的枝丫,总被人随手折去,或被牲畜吃掉。耕田的农夫,折一枝当鞭,凌空挥舞使牛;大田里捉了鱼,摘根枝条将鱼穿成一串;娃娃调皮捣蛋,妈妈折一枝抖舞训骂;贪玩的牧童,将牛羊往树上一拴,顾自去疯去野,任牛羊嚼叶啃枝……摧残若斯,哪能奢望它成大材呢。
尽管如此,年年春来,它都抖擞新枝新叶,春色不减。天气日暖,叶根陆续钻出一枚枚绿萼,萼片六七八片不等,七片居多。绿萼细长,好似小女子丫开兰花指。不几日,从萼心冒出绿蕾,宛若一粒粒青豆。绿蕾一天比一天鼓凸,绿色表皮绽开时,露出娇艳的花骨朵。原来绿色表皮也是花萼,它有双层花萼。花骨朵粉紫或粉红,像小姑娘嘟隆着小嘴。
某个清晨,人们从这棵树边经过,眼前突然闪亮,紫红的鲜花,一朵朵,一串串,次第开放,缀满了枝丫,树身肥硕富丽起来。花们好似一群精灵,乘着夜色悄悄而来,飞落树上,因为贪玩,留在树上了。行人驻足,一脸欢欣,打量那一树奇花。花开姿肆,纵情不拘。花朵肥大,外层五片大花瓣,薄如蝉翼,艳若羽衣,阳光里几近透明,脉络纹理,条清缕晰,仿佛是丹青圣手,妙笔勾勒出来的。花心一枚枚细长小花瓣,挨挨挤挤,不胜羞涩似的。中央一枝黄金花蕊突出,灿灿耀目。
这奇特的花,追随着太阳,晨开夜合,仿佛太阳是它生命能源。颜色也随太阳起落衍变,晨光中的紫红在夜色里变成紫蓝,融入天空一色。
我猜想,或许是花变蓝的缘故,人们把这花叫蓝槿花,树叫蓝槿树。蓝槿花可食。在那个物质匮乏年代,像我这样长身体的孩子,对一切可食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我曾吃过蓝槿花,味道酸叽叽的,回味却甘甜。难怪,牛羊都毫不客气,大快朵颐。如此一来,蓝槿花就遭殃了,蓝槿树自然也难长大。我始终觉得,造物将蓝槿花造得这般美,只可观赏、品鉴,哪能容人畜亵渎、摧残和践踏呢。但这样的情形,每时每刻都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发生,而且愈演愈烈。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树学名叫扶桑。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扶桑是神树,其高无比,上至天,下通三泉。太阳居住在扶桑树里,共有十个,轮流值日,一个升起,其他九个就在树上休息。不知为什么,有一次,十个太阳都升起来,植物枯死,河水干涸,赤地千里。后羿弯弓射日,射落九个,留一个供万物生长。
那一年,中石油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我家园,山河易形。推土机、挖掘机所经之处,老屋被拆除,祖坟被刨去,树木被伐倒,山梁夷为平地。宽阔的采气场上,钻井架高耸,像利剑刺破青天。巨龙般的输汽管道横行无忌,翻山越涧,伸向遥远不知处。
清明节回乡祭祖,欣慰自家老屋还在。我想起那棵伴我童年岁月的蓝槿树,它细长柔韧的枝条,不时在我记忆里轻拂,像在提醒我什么;它透明如羽衣的花瓣,不时在我心头绽放,抚慰我沧桑的心;它繁密的枝叶间,太阳每天照常升起,阳光暖大地,也温暖了我心房。
春草深深,把所有曾经熟悉的路径,都严密埋藏。从山梁上吹来一阵阵风。风不再清新,夹着臭鼻的恶气,划根火柴,似乎就会点燃。
循着依稀记忆,我寻找儿时的扶桑树。路易辙,水改道,连大水田都不复存在了,哪里还有扶桑树!
春阳依旧高照。没有了扶桑树,我不知道太阳是从哪里升起来的。
海上日出
文/小笨熊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这个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的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明亮的了。
这不是伟大的奇观吗?
日出
文/刘紫轩
早晨六点,天色蒙蒙亮,我就坐在阳台上等候一位尊敬的万物使者———太阳。当然也得看他演的戏———日出。
瞧!太阳终于露面了!他害羞地探出了半个脑袋。太阳刚一出来,万物都变成红彤彤的了。高楼呀,云彩呀,树木呀,一个也逃不过太阳那鲜红的光芒。太阳又悄悄地探出了他的大半张脸。顿时,天空被烧得火红火红的,犹如熊熊烈火。我清楚地看见太阳的边缘围上了一条金色的光圈,这难道就是他的围巾吗?
金色的光圈刚一来到,万物就被披上了一件大衣,金黄色的,可美了!
一朵金色的云彩飘啊飘,突然不见了。我把目光移向西边,它正在调皮地看着我。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干脆给我看了个戏法:它一会儿变成大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一会儿变成金旗,在随风飘扬;一会儿变成丝带,"嗖"一声,去缠绕太阳了……
过了数分钟,太阳还是害羞的不肯露面,我急了:"什么时候才能升起呀!太阳也真是的!"话音刚落,太阳"嗖"一声,升到空中了,这部戏结束了。
日出,真是一部好戏啊!
看日出
文/林椿
说到看日出,一般人会想到在名山大川之巅,或在辽阔无涯的海边,看红日冉冉升起,于是人们鼓掌、欢呼、跳跃。我也在那种场合看过日出,也领略过那种欢欣与激动的滋味,但给我印象最深并烙进脑海的日出,都是在寻常的地点。
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读高中,在杭州乔司部队农场结束了学军活动,步行返城。天蒙蒙亮约5点左右,我们就出发了。初夏季节,天气晴好,路边是大片的稻田和菜地,飘来阵阵稻谷清香,树叶和草丛上挂着晶莹的露珠。我们走着走着,天开始亮了,起初是朦胧的,淡红的色彩抹过天幕,继而黄色、金黄色、红色的霞光涌出,地平线的尽头,慢慢地、慢慢地太阳露出了半个身影,刹那间,金色的光芒照亮了天空和大地,大自然的一切在沉睡中苏醒了。田野、村庄、鸡鸣,一切都因日出而显得如此生动美好。我眯缝着眼睛,注视着这无与伦比的日出美景,眼睛湿润了,胸中涌动着莫大的难以言说的感动。
带队的老师也被感动,大声说"我们唱个歌吧,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于是,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走着、唱着,朝着太阳,一直向前。
如果说少年时那次看日出只是惊叹于日出的壮观美景,那么第二次在工厂宿舍楼平台上看到的日出,就有了点审美情趣与对生命意义的思考。那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很多青工清晨喜欢在6楼平台上早读和锻炼。从平台上往东望去,远远地可看到钱塘江。初秋季节,薄雾轻笼,江面上有早行的船在慢慢移动,空气清冽而甘甜。慢慢地,天空和江水相连的东方,霞光越来越浓、越来越亮,布满了整个天宇和江面,那金黄的太阳一点点、一点点地钻出了水面,终于腾空而起,通红的太阳经过江水洗涤,仿佛更加灿烂,更加辉煌。薄雾淡去,霞光万道,江水奔腾,生生不息。周围的伙伴发出了阵阵欢呼。我久久盯着那轮红日,心中忽然有一种跪下去顶礼膜拜的冲动。阳光、空气和水,这人类须臾不能离开的大自然的恩赐,你是那么的无私、慷慨,万物生灵一刻也离不开你,依赖于你而生存啊。
唐代诗人张若虚曾有一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引申改变一下,是谁看见了江边第一次日出?又是谁沐浴了江边这第一缕阳光?这千古之问,恐怕谁也难答。日月星辰,潮涨潮落,自有它的规律,人生于这天地之间,享受着大自然的种种恩惠眷顾,是否也应想想,在有限的生命中,为自己、为他人、为我们居住的地球,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