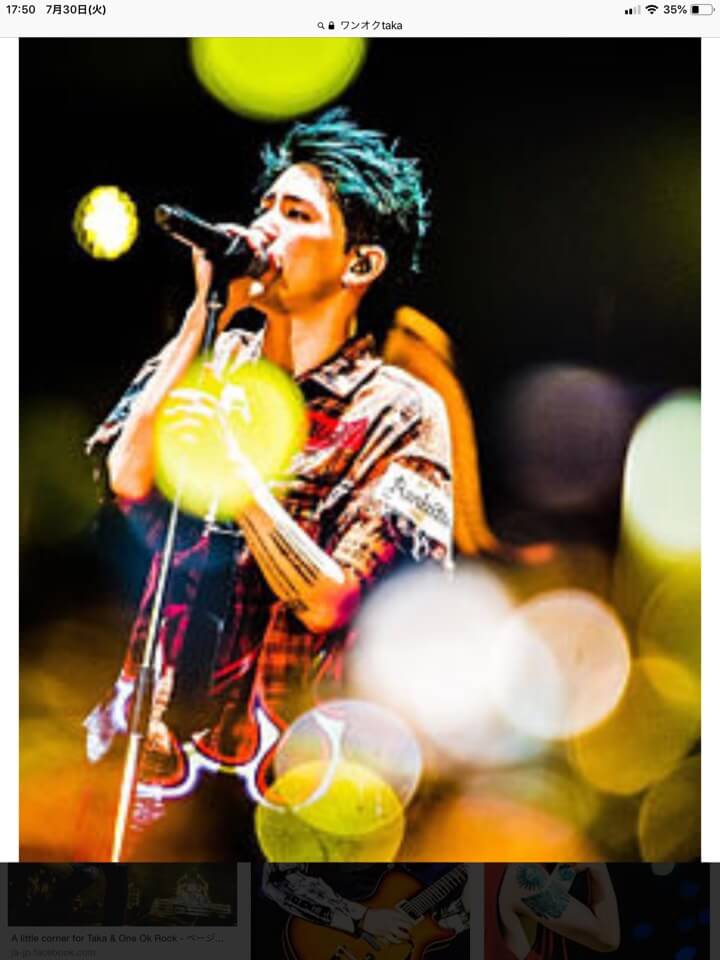守灵夜
清源县,离这里十公里的地方,今晚没有车了,我不可能过去,只能等待日出后前行。
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大的悲怆,夹杂着诡异,像在心脏里埋了一个手术刀。莫名其妙的来到自己的家乡,来到这个死城一样的地方,接二连三的死亡,还有这里面无表情的人群。
为什么要悲伤?得知舅舅死讯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悲伤,而从看见表妹尸体那一瞬间,阴霾的情绪就没有间断过。不就是两个几乎素未谋面的远亲吗?我实在跟他们一点感情也没有,可他们的死带来的绝望为什么会在这个诡异的夜晚把我撕裂。
我吞了几个饺子,尝不出它的味道,喝掉剩下的酒,为死亡干杯。我拿上行李,结了帐,走出这个伤心的小店,准备找一个旅馆下榻,为明天的善后事宜做准备。
在路上好几股阴风袭来,感觉万箭穿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来不及想为什么往回走了十公里才走到家乡,列车员不是说往前才对吗?我来不及想这些,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这铁轨是绕着圈铺设的。
在大街上走了五分钟,在小巷的拐角发现了一家比较安静的小旅馆,它看起来十分破败,油漆早就从斑驳的墙壁上掉光,旅店两个字的弥红灯也灭了一半,天又下起雪了,我赶紧钻进这家疑似鬼店的旅店。
在前台的是一个面色惨白的姑娘,她的眼睛很小,瞳孔简直还没有针尖大,我默默的给她出示了身份证,她象征性的抄下了号码时我才知道在这种鬼地方住宿根本用不着那玩意。我要求她给我一个干净些的房间,她眼皮也不抬,把钥匙生硬的扔在了前台老旧的桌子上。
我拿着钥匙上了二楼才发现她给我的是楼道最顶头的房间,以前听说过不少旅馆最顶端的房间闹鬼的传闻,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每次在这种房间睡的时候总能听到枕边有人暗声低语,说一些前世今生之类的鬼话,尽管他听不清那个鬼魂说的是什么,但他发誓这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我不是个有神论者,所以我不信这套封建迷信,于是我打开门,走进房间。这里有一股潮湿的气息,我觉得可能是前一个房主时掉下的汗还没有蒸发完。
还好它除了这股骚气外还有张比较柔软且干净的床,我为自己烧了壶水,躺了下来望天花板,感觉自己的身体有点不对劲,我发现我的右脚已经毫无知觉。
我坐起了身,用手指使劲捏自己的脚掌,它却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我从旅行包里取出了备用的牙签,向脚面轻轻的扎去,一样的毫无知觉,它已经麻木了。
在雪地里走的受风了,如果不去医院治疗,血液持续几小时循环不通的话我的脚会废掉,年纪轻轻的我将被截肢,成为一个废人。我不想看到自己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我得去医院看一看。
前台那个面无表情的服务员告诉我这个小镇只有一个医院,我顿时觉得庆幸这地方有的是医院而不是某个开不出收据的私营诊所。
二十分钟后我走到医院是却发现这医院其实跟诊所差不多,它是一个只有二层楼的独门独院,院子里居然长满了野草,大厅的门开着却看不到一个人,只有微弱惨白的光。
我走了进去,整个小镇很阴冷,而每个城镇最阴冷的地方当属医院,而我身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