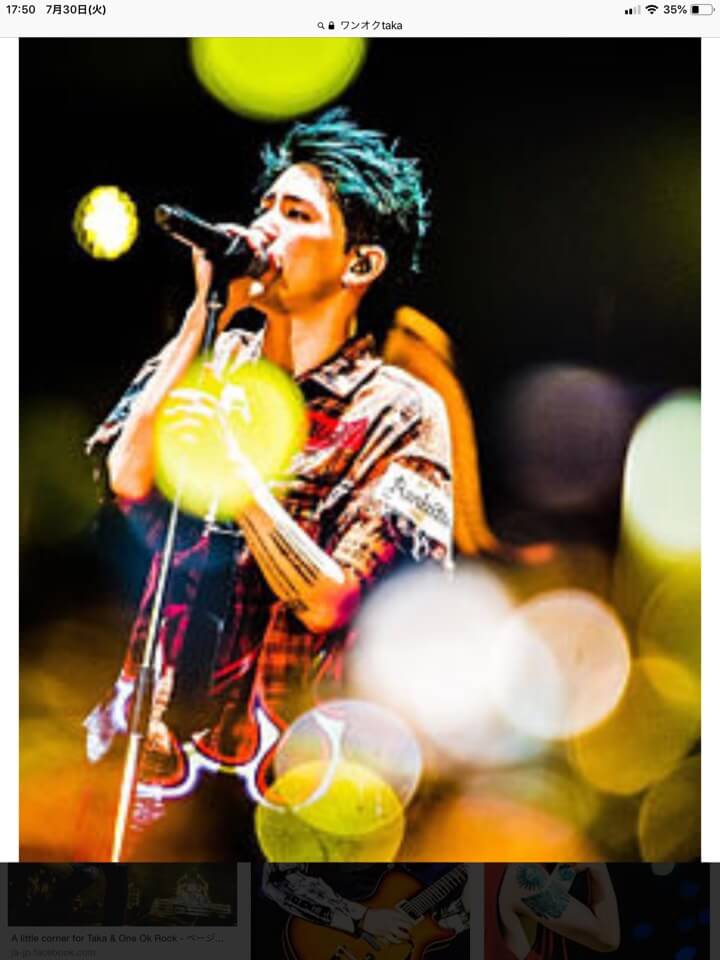凌晨3点过6分
我边听着小康乱扯边拿着茶杯喝了口茶。问小康:你写了一晚上论文不困啊。小康说不困。一想到这个肢解的案子就感兴趣。我说我也知道一个案子跟你说说吧。小康打断我说:我去烧壶热水。你快帮我改论文。然后拿起水壶就奔门外去。
如你说见。我的室友不但大半夜竟是说些令人浑身发毛的话。而且还喜欢打断人。但平心而论。他在专业的专注度和事业上比起我来是强很多。我大学读的是物理学。因为高等数学总是不及格改修国际政治学。总算勉强毕业。从事了某政治报的编辑工作。因为配错了一位头头的照片。被定性政治错误开除。后来听说这位头头被双规。但依然没有单位肯接纳我。现在为某国史网的一些大学教员当枪手写写论文赚点钱。但如你所知。国史论文即生涩难懂又无人问津。所以英语好的翻译一篇英文论文的价格。我要写六篇论文才能赚到。
我拿起小康桌上的烟出门准备去楼下透透气。这幢小楼并不高。是一个有些年头的大学宿舍楼。叫明德三栋。本来是老师住的。因为太破旧就成了一座向外出租的宿舍楼。楼道里什么都没变。甚至保留了门卫室里的韩国老头。那老头有个习惯。晚上不睡觉。但是我早上也没见他睡过。具体什么时间睡我也不曾得知。只知道门卫室有张他睡觉的弹簧床。每夜每夜的坐在床上盯着桌上那台又破又旧的小电视看。我敲敲门进去。对他笑了笑然后递上小康的万宝路。老头点上烟接着看电视里的娱乐节目。如你所见。拿烟下楼并非是我要抽。我这人不抽烟。倒也不是不喜欢抽。出国前我应聘了一个传染病私立医院的网络SEO工作。负责这间医院的搜索引擎优化。也就是负责给医院当网络专职水军。那时我抽烟成瘾。上着班就偷跑到走廊里抽一根。有时还碰上偷跑到走廊给老婆或情人打电话的主管。医院找人拍了部广告宣传片。患者凑不起来。主管把我叫去凑数演来此医院治疗得当的肝癌患者。后来有次在走廊抽烟。一个小姑娘认出我来说你不是做医院广告的那个人吗?我说是。小姑娘说我妈每次看那个广告就说真可惜挺年轻的小伙子就得肝癌了。我说我是假患者。小姑娘说哦原来如此。你在走廊干什么?我说闷。抽根烟。她说能教给我抽吗?小姑娘是高中生。但长像成熟漂亮。看不出年龄小。我就耐心教给她怎么抽。临走时互换了手机号。以后经常我在走廊抽着。她就跑过来夺我烟。有时我到了还会给她打电话叫她来。我们就这样一根烟一人一口边抽边聊。听她说了很多学校里追她的男生的事。这样大概有一个月的光景。遇上非典。领导让网络部的暂时在家里工作。那时非典很严重。医院全都封锁了。同事们传言医院里死了一个高中生小姑娘。最近咳嗽加重。我一直以为抽烟导致。听到这个消息吓了一跳。非典过去后我咳嗽也早就好了。可是还是不放心就把名字给了主管让他帮我查一下。隔日主管来找我。告诉我死的确实是她。我说我是不是有可能传染非典了?主管说那小姑娘不是得非典死的。艾滋病。
后来我做了个全面检查。虽然没大碍。但晚上睡觉时总梦见她来找我要烟抽。最后就把烟给戒了。
这时候老头趁着电视放广告间隙转过头。笑着把他抽的那支烟递给我说:抽一口?
我问老头你知道那个分尸的案子吗?老头说倒是没听说。我心想室友小康又想要胡说骗我。老头说这栋楼风水好。不死人。我心想我韩语一般表达不明白。老头又耳背。索性不想跟老头再多说话。老头拽住我说:来咱们喝一杯。说着从抽屉里拿出瓶烧酒。跟老头喝了起来。老头边喝边说这栋楼倒是没死过人。旁边那栋死过。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想老头不是老糊涂了就是喝酒喝糊涂了。旁边那栋是这个学校的食堂。我说是食物中毒吗?老头说不是。我也是听说。那时候我还在庆北老家。但是这事绝对是真的。当时梨花女子大学来了一帮女孩子第一次做学生交流。安排进明德三栋老师宿舍住了。要呆一个月的时间。你看三楼楼道里那面大镜子。就是当时梨花女大赠的。那些女大来的学生中有一个女孩子跟这个学校的一个男学生好上了。当时韩国是军统**。很腐败。学生全都不上课。天天上街游行。总统全斗焕就下了禁令。不让学校上课了。军队到处抓人镇压。结果那个男生晚上没回学校。
老头正说着。送外卖的敲大铁门。老头拿着一大串钥匙过去开门。老头说现在学校为了安全天天晚上要我们都锁上大门。晚上你们租房子的总定外卖。我也睡不好。今天还算好。就开了这一回门。然后从楼上走下一个大叔。接过外卖匆匆上了楼。我想夜里订饭是够烦的。就跟室友小康夜里总吃炸鸡把我饿醒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