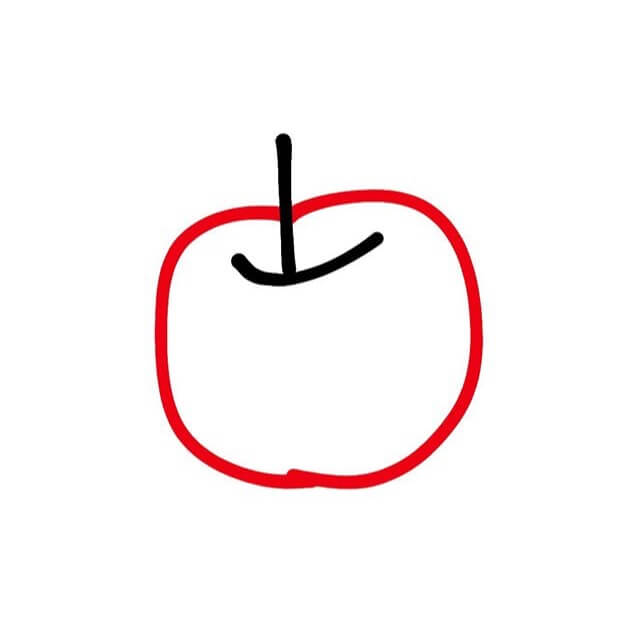死结疙瘩
过去
这件事似乎发生了好久,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并不住在这里,后来我老了,便被儿女囚禁在这个钢铁森林里,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浓浓烟尘将整座城市包裹,天也不蓝了,草也不绿了,总是觉得什么都改变了,都不对劲了。
几十年前,我主动放弃大城市的高薪,来到一座小村庄工作。那时候我在山村的一个小医院里上班,说实话,那里根本不能算是医院,只是一个两层的小诊所,没什么医疗设施,药品也都是一些初级的治头疼脑热的药片。
整个医院里面除了我,就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老护工。我在那里当护士。
诊所的二楼是病房,里面住着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有的是被家人遗弃,有的是一些流浪汉。
平常医院里没什么人来看病,医生很懒散,平常只有中午才出诊,一小时不到又出去了,大晚上喝得醉醺醺的才回来。这里的村民一般没有什么实在受不了的大病根本不会来看医生,这里药品的价格就够他们一天的饭钱了。
我的日常工作并不像大城市的护士那样,给病人打针嘱咐他们吃药,而是给那个老护工打下手,打扫做饭洗衣,基本上老护工不愿做的事我都要做。我不像是一个护士,更像是他们的保姆。
医生年过半百,长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经常占村民的便宜,不是少给就是用过期的药片以次充好,为此村里不少人都因为药量不够或者耽误了治疗时间而病重或丢了性命,当然那些死者家属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或许家属们觉得,少了这些病秧子就是少了身上的累赘,各个都不曾露出悲伤的样子。
他也因此得了不少家属的红包,虽然钱不多,在这里生活却还是足够的。我们也拿过他的钱,他说,只要我们照着他说的做,钱自然是少不了的。
现在
护士端着药来到我的房间,我看了她一眼,她将药片放在床头柜上,我熟练地将药片假装吃下去,其实是偷偷地藏在了手心里。她走后,我便将药片用白水粘在了床下。
自从我来到这里,护士给我的所有药全都被我粘在了床下。
我也当过护士,我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病,只是这个医院挂着救死扶伤的幌子,其实是在用慢性毒药害死前来就诊的人。而无知的外界却用各种讨好的话语来炒作这么一个不真实的医院。
瞎眼女人刚睡醒,她最近睡得越来越多,似乎也越来越疲惫。她蜷在床上小声地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故意说给我听。她说她做了一个梦,然后继续絮絮叨叨地讲那个我听了好几十次的梦境内容。
我小心地从床上下来,走到她旁边,看着护士放在她床头柜上的药片笑了。我像往常一样,换掉她的药。那些药是我趁护士不注意的时候,从她的小铁架车上偷来的,然后我再假惺惺地劝她喝掉。
直到她入睡,我站在她的旁边,小声说着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她不知怎么了,猛然说了一句:“那些跳楼的人,是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惊了一下,几十年前,我也听人说过一模一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