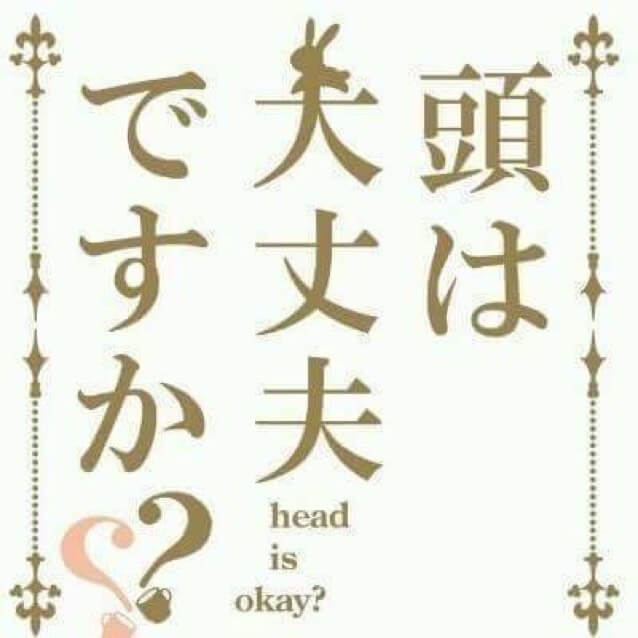渭南人和馍
馍是高贵的、有品位的!馍的品位从来就不输给米饭、面条、饺子。很多人认为馍普通,觉得这东西土气,白白的,圆圆的,嚼起来没有多少味道,甚至不佐菜肴难以下咽,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馍,没吃出来馍的那股麦香。澄城人以馍为主食,米汤和面条辅之,扩展到整个渭南,大抵差不多,经常会听到:你能咥馍地很!今天看来,很多人连馍都咥不了,咥不出个所以然来。
小麦从西亚、中亚传到中国,传遍世界,目前是全球40%人口的主粮,古今中外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吃法。在陕西渭南,特别是渭北澄城、白水、蒲城、合阳一带,以蒸馍为主。
渭南人只要到了外地,吃哪里的馍都觉得不香,都没有自家的馍好吃。外地人,特别是不擅长蒸馍的外地人就在心里骂这帮贼矫情。其实,渭南人真的不是矫情,就是馍吃得多了,嘴刁了而已。贵州的茅台镇家家户户酿酒,抿一口就知道别人家和自家的味道不同,渭南人的馍同理。所以,没吃过一万个馍——最少三五年的量,就没有评价和否定馍的资格。吃馍吃精了的渭南人,咬一口就知道面粉是陈麦,还是当年的新麦。
渭南人蒸馍是不用发酵粉的,我祖上那会儿也没有,也不放碱,用的是自家做的酵子。每年秋季,把新糜子磨成面,拿三两个上一年用剩下的酵子泡在水里,然后用这个老酵子水把糜子面和匀,做成一个个面饼晒在太阳底下让它自然发酵,这就是下一年的馍引子。酵子干透了,用线从中间穿过去,然后挂在灶台边上,就像是一串桃酥饼。酵子有点酸酸的怪味,小孩子不爱闻。
渭南人蒸馍和面时只放一点酵子,然后就交给温度和时间。发面是个技术活,夏天晒在太阳底下,半个把小时就发好了,冬天却要放到热炕头上,用棉被把面盆捂好。面发不到,蒸出来的死面馍就是个瓷疙瘩;发过了,馍暄乎得像蜂窝,但吃到嘴里发酸。渭南人只有大意了,面发过了,才迫不得已用一点点碱面揉在面里,起个中和的作用,但这种馍咬着没劲,敢再掉到米汤碗里,两秒钟就成个软塌塌的泡芙。揉面是个体力活,“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这条祖训虽然只讲对了后半句,但一个“到位”的“到”字,却把揉面讲得充分而完美。
家里平时吃的馍,形状比较单一,一般是带有流线的长方形,家庭主妇偶尔拿捏不准,剁馍时多出一两个放不进笼里,干脆捏一点盐和花椒叶,把剩下的面头重新揉了,直接撂进灶膛里烤“骨角馍”。这时,家里的小儿孙便会跑来守在红红的灶火旁,眼巴巴地等着。若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那就是展现蒸馍才华的时候,各种造型的狮子、老虎、“绽花馍”是对主妇最大的考验,而馍大、面白、虚软、好看是基本标准。在澄城,过年时要给灶神蒸“枣山”,给其他家神蒸“供供”、给长辈拜年蒸“包包”,给儿子、孙子蒸“魂饨”、给女儿、外孙子和族里的小孩子蒸“鹣鹣”,造型和寓意全都不一样。拿“魂饨”和“鹣鹣”来说,里面包一点调味馅,外形都是吉祥的小动物,眉毛是用剪刀剪出来的,眼睛是用黑豆或花椒籽嵌进去的。眉、眼有了,就传神了,当地有个词汇就叫:眉眼(mí nian),指人的表情,带有嫌弃的贬义。过年时,晚辈要给长辈拜年,长辈则要给晚辈送“鹣鹣”,而“魂饨”是只给主人吃的。当地有一句谚语:“正月二十三,麦子泡枣山”。麦子泡是一种澄城小吃,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除了填饱肚子,馍里更有澄城人、渭南人的血脉、亲情和文化认同。
人口多一点的家庭,三五天就得蒸一锅馍,人口少一点,十天八天蒸一锅。秋冬时节,馍一般都放在馍盆里,澄城的尧头窑专门烧制这种陶瓷盆,有大有小,大的可放进一锅馍,遇到过事,那就直接往瓮里放,三五百个都没有问题。夏天,馍会被放在通风透气的篮子里,挂窑洞里的高处,为尽量防止风干,一般都用笼布盖上。在澄城,“攀得着馍笼”是一句戏谑语,意思接近于“翅膀硬了”。
澄城人以前一天吃两顿饭,早上九十点钟一顿,晌午两三点钟一顿,早饭千年不变:米汤、馍,外加一碟辣子或咸菜;中午一般是面条,也可能是麻食。至于晚饭,很少吃,确实饿了,还有一道地道的“名优小吃”——煎水泡馍——其实就是把凉馍掰成块,浇上开水,加点盐和油辣子,所以周边县市有一句话描述澄城人:澄城老哥,煎水泡馍。
我朋友虎虎是蒲城人,有一天他媳妇给我们铺排虎虎:“我们家上海人啦,奶奶以前是开餐厅的,就没有我们家不会做的菜,可虎虎总说我们的饭不好吃,说我们不会蒸馍。简直搞笑哩。”我心里想,她还真冤枉虎虎了,那就是个馍肚子,渭南人都是馍肚子。
对于渭南人,肉可以没有,菜可以没有、米可以没有,馍一定要有。世代只吃馍,渭南人就成了蒸馍的高手,吃馍的专家。渭南人创造了各种吃馍的样式,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夹着吃、做成麦饭拌上蒜辣子吃……关于渭南人和馍的话题永远写不完,因为馍连着每一个渭南人的根,黄土高原上的祖祖辈辈就是为了馍而战天斗地。渭南过年,准备工作的收官之举就是专门用一天时间来蒸馍,当灶台上蒸馍的水汽氤氲而起,伴着朗朗的笑声,渭南人的年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