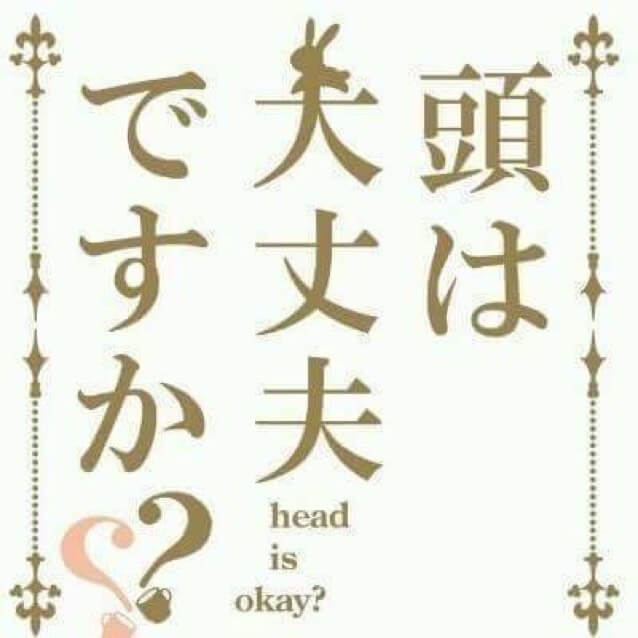你有炙热,我有紫苏
南方的夏,是个让人爱得痴迷又恨得牙痒的季节。
有人爱夏天,瓜果飘香,菡萏垂荣,萤火飞花……而另一厢,炙热如火,似不速之客,不管不顾扑将过来,烫你个没商量,令人尴尬又无奈。
没人知道,夏之于我,每每都是要鼓足勇气,才能安然度过。尤记得小时候捂出一身痱子的难受,青少年顶着烈日劳作的辛苦,中年后空调吹到颈脖酸疼的无奈……有时候会异想天开:何不将夏掰成两半,各取所需,一半给喜欢它的人,尽享“热”情,另一半给讨厌它的人,避暑独处?明知不可为,于是退而求之,自备纳凉藩篱,练就心静自然凉。
偶尔赤脚踏在炙热的乡土上,在房前屋后寻觅食材,愉悦冲淡了脚底的不适。折耳根在屋檐下的水沟蓬勃生长,一片绿茵,掐下它的嫩芽凉拌,解暑又消炎,是我最喜欢的。混杂其间的,有如苋菜一样的稀罕物——紫苏,突然冒出来,给人猝不及防的惊喜。紫苏,极美的名字,如诗经中曼妙的女子般,羞涩紫红,香气馥郁。相传华佗采药时,见一水獭吞吃了条鱼中毒,肚胀如鼓,显得很难受。但等它爬到岸上,吃了些紫色草叶后便没事了。于是他给草叶取名为 “紫舒”,即紫色的令腹中舒服的草。后流传日久,渐渐变成“紫苏”,大概是音近的缘故吧。
“海棠花下生青杞,石竹丛边出紫苏。”想起宋代汪元量的诗,紫苏在眼前一下子入了画,你看它,青紫渐变,色彩神秘,随性生长,低调圆融。像画家笔下丢下的一粒“种子”,放在哪儿都能入眼,幽香宜人。更让人欣喜的是,当你需要时,随手掐几片叶茎,用以解表散寒、行气和胃,药到病除,故颇受古代医神、医圣的青睐。明代李时珍曾记载:紫苏嫩时有叶,和蔬茹之,或盐及梅卤作菹食甚香,夏月作熟汤饮之。小时候生病,小孩捏着鼻子灌紫苏汤是常事,如今,用它来凉拌清暑,平添乐趣,冲淡了夏的苦味。
我边掐边寻,惹得邻居大嫂近前打趣,先是惊讶地“噫”了一声,后忍不住问:“这东西也能当菜吃?”我蹲在沟边点了点头:“嗯,好东西呀,凉拌很好吃。”她摇摇头,笑着揶揄:“城里当真是没什么吃的了,农村的野草也成了山珍海味。”我也笑笑,附和:“还真是野草味香呀”。摊开掐过紫苏的手,不仅染上淡淡的紫色,更有一股扑鼻的浓烈的香,与折耳根的土腥味交织在一起,鼻尖就有了安静祥和的乡土味儿,从远古至今,聚神提气,带劲得很,熟悉又难忘。
都说,时光荏苒,荏苒就是紫苏茂盛的样子,作为野草的紫苏,春生冬谢,年复一年,它的平和与圆融的性情,与夏的炽热、躁动相佐,自带和谐亲切自然气息,入眼入画,你若随意一唤,心底便生柔软芬芳的诗意!
我特意挖了几棵,栽在城里住处的阳台上,有了它的陪伴,这个夏天,你有炙热,我有紫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