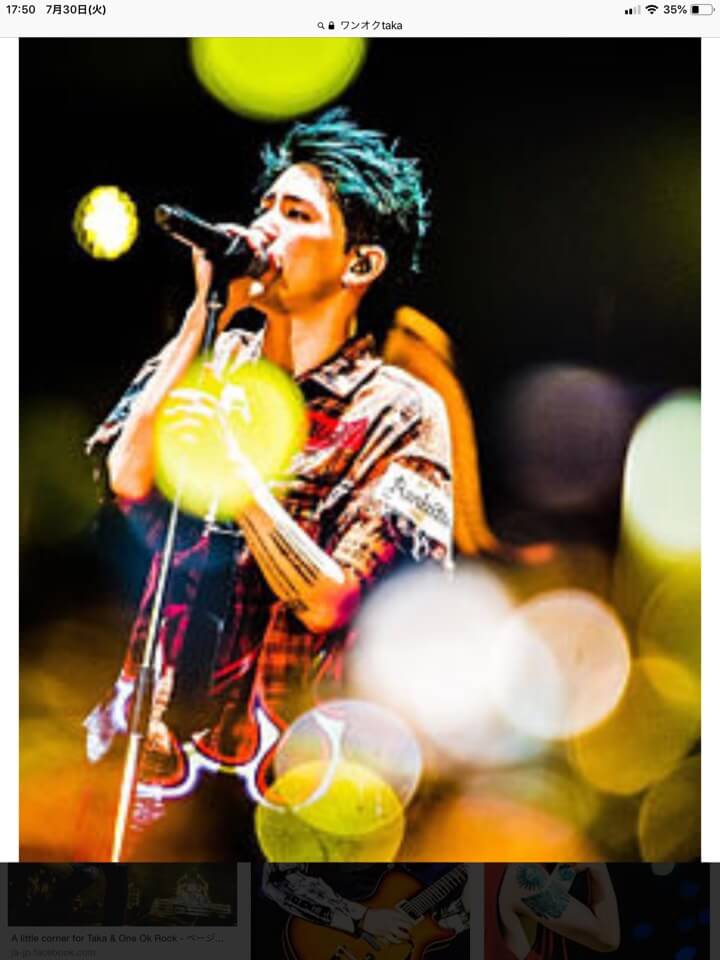人间年味长
一年1000多顿饭,飘散着食物的至真美味。有一桌饭,满足着团聚之人的念想,这是一桌年饭,十分乡愁中,烘托出新旧之年交替的高潮。
母亲在腊月里开始忙年,她几乎是一辈子穿梭在油烟滚滚里,忙年,是她精神世界里的一种支撑。母亲的忙年,拉开了一家人团聚的大幕,尔后是一家人在年的灯火下,围坐在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边,食物发酵着年味,也凝聚着亲情,让年的灯火可亲。
在过年的食物里,有着古老基因的遗传。比如一个煮熟的腊猪头端上八仙桌,开始对逝去祖宗们的郑重祭奠,想象着他们腾云驾雾而来,与开枝散叶下的子孙们团聚,一同品尝着人间美味。一块豆腐,在母亲手掌的旋转中,豆香盈盈,清白的身子投入油锅中哧啦一声,转瞬被炸得金黄绵软,用蒜苗炒豆腐,蒜苗是乡下刘嫂子从地里扯来送到城里我家的,还裹挟着老家的露水气息。
一桌年饭上,母亲做的凉菜,碟碟盘盘中就有好几样,凉菜是对热菜的一种呼应,一道凉拌三丝,豆芽、胡萝卜丝、海带丝,一眼望去,喜气洋洋中俨然有着一个寿翁的气派。至于热菜,有10多种,保留菜是炸春卷,它从古时的春饼绵延到我家的团年餐桌上,一口咬下去,新春的气息扑鼻而来。还有母亲头天夜里就在老炉子里煨的芸豆蹄花汤,汤里漂浮着细碎葱花,炖得软软的猪蹄子,用筷子轻轻翻转,骨肉相连的雪白中夹着一层粉嫩的红,那是瘦肉部分。把软烂的猪蹄子挟入嘴里,卷动的舌头上来亲昵拥抱,还没等牙齿前来相助,从骨头滑落的肉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再喝一口奶汁般的蹄花芸豆汤,通体舒泰。还有红烧狮子头,母亲亲自去菜市场挑选了五花肉在菜板上剁成肉末,厨房里响起的“嘭、嘭、嘭”声,这也是新旧年之间追赶着的声音,肉末配上荸荠、香菇、豆粉等食材做成丸子,先炸后煮,出锅后一股扑鼻香味缭绕了整个房间,醇香味浓的肉圆与汁液,令人食欲大振。
年饭上,四面八方的亲友们围坐在一起,山水迢迢中的重逢,食物首先打开了味蕾的记忆,它是最贴心的相随。吃喝中笑语欢声,美食通过胃的蠕动穿过柔肠,娓娓交谈中,面对面传递着一种最宜人的温度,这是真实可触的团团圆圆。一些亲友相见,在热腾腾的食物中也相互发现了彼此的眉上挂霜,感叹着聚一次少一次了。去年腊月,我回老家在山道上遇见拄着黄杨木拐杖的堂婶娘,婶娘从衣服口袋里摸出几片芝麻糕塞给我说,吃,快吃。82岁的婶娘嘴里大牙全掉了,瘪着嘴说话有些漏风,她拉着我的手一直舍不得放下。婶娘说,春节我来看你爸妈。正月里来是新春,堂哥陪着婶娘颤颤巍巍来到母亲家里,她挎着一篮子米豆腐,是婶娘和堂哥用石磨碾出后手工做出的,婶娘还送来了一罐腊猪油。夜里,母亲听见婶娘在梦呓,趁热吃,趁热吃。我春节去婶娘家,婶娘夹给我一块肉,也是这样跟我说话,我在她幽蓝浑浊眼睛的注视下,接过肉愉快吞下,老家山山水水的地气也在我体内弥漫开来。
春节里,我去乡间走亲戚,一家一家地挨个拜年,遇上长者,鞠躬抱拳,递上一个红包,这是朴实民风的洗礼,也是传统礼仪的生根。爷、伯、叔、舅、婶、姑、姨、侄、甥,这些称呼里有着血脉绵延成的大河,也有着藤藤蔓蔓中牵起的剪不断的关系。
一扇扇斑驳或簇新的房门上,也贴满了乡间笔墨之人手写的大红春联,它对新年日子里寄托着红红火火亮亮堂堂的希望。我的一个表叔,一到腊月的年关,就提着装有笔墨纸砚的竹篮在村里转悠,帮村上人家免费写对联,除夕那天,家家户户贴上了我表叔写的讲究韵律平仄的春联,字体遒劲笃实,一直到第一声春雷从云层传来,犁铧掀开潮湿的稻田泥土,春联还是鲜红喜庆的。
我在城里的老友杜先生,这些年每到春节,就要在纸上写下一些名字,那是当年住在老街老巷里老邻居们的名字,他在腊月里开始联系,一家来一个代表,请他们春节里聚一聚,一起热热闹闹吃个团年饭。杜先生还是一个读书人,家有藏书上万册。人在老,书也在老。春节里,杜先生再次摩挲着满壁书架里一些老态龙钟的发黄旧书,这些旧书仿佛稍一用力就会粉身碎骨,书页间有光阴积下的粉尘簌簌落下。我在杜先生的书房里嗅到了书香,感觉这也是一种古老而醇厚的年香。
在这些人间至纯至真的年味里,饱含着质朴的情感,奔跑而来的,是新年降临的晨曦,是万物生长的喜悦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