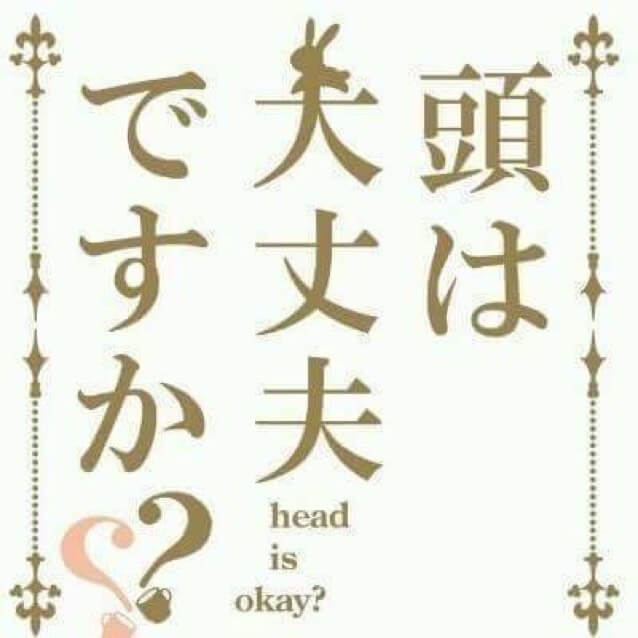外婆的嘱咐
记得我还是幼童的时候,外婆曾问我:“你长大以后,会抽空到外婆的坟头拔拔草吗”。
而今,外婆去世已经三十年了。
外婆出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是在旧社会过了大半辈子的人。她前半辈子的命很苦,不满10岁就没了爹娘,叔叔收留了她,但终因家境也不好而不堪重负,就早早给她找了婆家。这样,刚过11岁的她就做了人家的童养媳,对象是一个病恹恹的男孩。在那个准婆家,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安于总算有了“终身托付”;婆婆虽然严厉刻薄,但还算能干。外婆天生聪慧而又勤劳,虽然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小心翼翼的劳作,却学到了许多生活技能,为日后过日子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可是那个男孩却没能活到成年。
外公勤劳与智慧兼备,在农夫中可算是个能人,极受人尊敬。他不苟言语,却精通农事,农村中的活计无所不能,加上他的勤于劳作,在他们家那有限的田地上总是呈现出“五谷丰登”。外婆是个持家能手,她总能把暂时吃不完的鲜活农产品作进一步加工,以便于储存保管。外公与外婆的结合,真可谓天作之和:“男主外,女主内”。因而,即使是在那个产品经济年代,生活物资的季节差别和丰欠年份的差别,在他们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中总不那么凸现,还常有拿出来接济乡邻的。外婆与外公相处得极其恩爱,家境也渐渐殷实,那个家庭极令人羡慕。但不尽人意的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外婆尽管生育了10多胎,却到了40岁时,我母亲仍还是她的独女。
外婆平生博爱,与邻里乡亲都相处得极其和睦,且乐于助人。外婆很注重加工储藏一些治病单方和干(腌)菜,譬如,她把很不起眼的菖蒲根洗净切片,用盐腌着,用于祛寒;将别人只会当垃圾抛弃的青菜头茎削去粗皮,腌盐,晒干,供服中草药时需要忌口的人佐餐,等等。乡下缺医少药,那时,这些东西很顶用,因此时常有人来索讨,外婆总是有求必应。我小时候还常常看到,当她遇到有乡邻缺吃少穿时,便从自己家里拿出粮食或旧衣物来接济别人,表情是那样的自然,是那样的慷慨、无私。她的这些乐善好施,慷慨助人的品德赢得了乡邻们的信赖,村里女人们在生活上或感情上遇上什么为难事,总爱找到她或诉说、或求助,甚至家里的母鸡下蛋时出不来,都来请她解决;同时,她也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过路的人拐个弯都要来和她打个招呼,给个问候。
我是在娘胎时就受到外婆精心呵护,出生后是依偎在外婆的怀抱中长大的,她对待我,真可谓“含在口里都怕化了”。记得小时候,在冰天雪地疯玩,睡觉了,手脚冻得还像冰棍一样凉,外婆总是把我那双小脚捂在胸口。我都上高中了,回到家,放下书包就会直奔外婆家,若喊三声还没听到答应,就会哭。如此祖孙感情岂用“血浓于水”能够形容?我心里当然明白,老外婆是多么想我陪伴在她身旁,直到她终老。可是,她把我捧到了18岁,我要参军了,那将是分别后三年不得一见啊,外婆深明“服从国家需要”的大道理,临别嘱咐只是“安心干,不要挂念我”,此时却没有提及“上坟头拔草”这样的最低要求。
我对外婆的愧疚是终身的。我没能好好地孝敬她,甚至在她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去送她最后一程。那是我还在部队,且正在上大学的时候,她硬是没让我知道。外婆在弥留之际,还在想着不能使我因牵挂她而影响工作和学习。
外婆的形象是崇高的,她所表现出的品德,正是当今我们营造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个人素养。外婆在我身上花费的心血,我永远铭记,不可磨灭:我的成长和性格养成,都得益于外婆的敦敦教诲,或潜移默化。每当回忆起外婆对我的恩德,我感恩之心潮澎湃。现在我自己也已为人祖辈,在感恩外婆的同时,也强烈地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担负着传承和弘扬前辈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的重任,我们的言行举止,或高尚或低俗,或文明或粗野,都将在后生晚辈面前留下印记,对社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