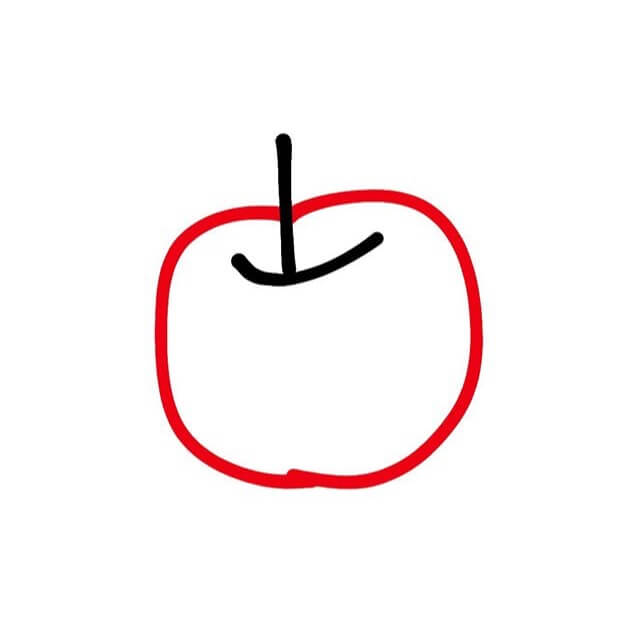怀念祖母
逢年过节,父亲总要在老家拜神的,拜完天神,再拜祖先。
冬至回家,父亲对我说:“给你阿婆上柱香吧。”
我依言焚香奉烛,躬身而拜,抬头看到祖母的遗像,照片上的老人目光慈祥,双唇微启,像是有许多话来要对我们说。
岁月如梭,何曾停留。祖母离开我们已快二十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不时闪现在眼前,时常引起我深深的怀念和眷恋。
记忆中,祖母有着一头银白色的头发,那发丝柔顺、光滑不掺一根青丝,童年时,常看祖母躺在后院的竹椅上,淘气的我爱爬到她的肚皮上,缠着她给我讲古,祖母肚里有许许多多的“古”,永远也讲不完。冬天,我们在院子里晒太阳,阳光照在祖母一丝不苟的发丝上,散射出来的光是银色的,十分好看。
幼时最爱看祖母梳头,收集她发梳上的每一丝年华白。清晨的阳光斜过老屋的木窗棂,被分隔成几道细长的光带,光里有轻尘飞舞。祖母坐在窗前,解开蓬松的发髻,那一头银丝几乎及膝,她侧着头,用一把木梳子细细地把头发梳理一遍,然后拿手指抹一点儿茶油,顺服的头发被绕到脑后梳成发髻,再用一根银簪子别起来,纹丝不乱。
在我少时的记忆中,祖母是温和可亲的,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父母每日忙于生计,照顾孩子的任务,自是落在祖母身上。幼时我体弱多病,是祖母常常为我煎熬中药。我畏中药的苦,总是不肯痛快的喝,母亲着急起来,捏着我的鼻子就要往嘴里灌,我怕得大哭。祖母把药碗揣过来,不知从哪里摸出一粒糖:“乖,快喝了,喝完有糖吃呢。”我于是止了哭,乖乖把药喝了。病好后,又是祖母寻来五指牛奶皮(土黄芪)和山地豆藤给我煮开胃粥。祖母常说,我吃了她煮的开胃粥,就“想吃”了,脸儿也红润了。那时候最爱吃这个开胃粥,拿筒骨一起熬,味道那个香啊,至今仍让人念念不忘。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小孩子并没有什么零食,姐妹们老觉得肚子是饿的。白日里,常会有石磨米粉挑到村子里叫卖:“米粉咧,有石磨米粉——” 卖米粉的叫卖声响亮悠长,充满诱惑。我们肚里的馋虫都被勾出来了,磨着祖母要吃米粉,祖母心疼我们,可是又拿不出钱来,最后只好从米缸舀出两碗米,用布袋装了,让我们拿去换米粉解馋。自然,这拿米换米粉的事儿,只能偶尔为之,还得瞒着我们的爸妈。有时候家里的米缸也快见底了,祖母就对我们说:“那米粉是臭馊的,我们不要吃。”我对祖母的话深信不疑,跑去对卖米粉的说:“我阿婆说你的米粉是臭馊的,我们不吃。”卖米粉的也不说啥,笑一笑便把米粉挑走了。我望着挑米粉远去的身影,偷偷把口水咽下去。
生活中,祖母对孙辈爱护有加,却并非没有原则的溺爱,姐妹们若犯了错,照样得吃苦头。印象最深的一次,记得是在我六岁那年的夏天,不悟水性的几姐妹偷偷到村里最深的大水塘玩水,祖母得知后,气急败坏地赶来,把几个浑身湿透,玩得疯颠的丫头抓回家,臭骂一顿,并扬言要告诉父亲。我们害怕极了,父亲可是严禁我们去水塘玩的啊!晚上父亲回来,得知我们犯禁后果然大发雷霆,将我们姐妹几个集体饿饭,以示惩戒。
夜里,我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祖母问我:“丫头,是不是饿呀?”我可怜巴巴地说:“好饿。”祖母悄悄地起来,到厨房捧来一碗饭给我吃。记得那饭有肉有菜,与其说是吃剩的,不如说是故意给留下来的。
那时候,姐妹们争着和祖母睡,祖母最疼我,总是把我留在她的床上,把几个姐姐撵到一边去。我和祖母同铺而眠,直到上初中。
一九九六年冬天,我在省城上学,接到家里的电话,告诉我祖母病重。我听到大姐强忍悲伤的声音,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赶回家,一屋子全是至亲的人,面上满是悲伤,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祖母已经不在了!我自觉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有很多话要对祖母说,但此刻什么也说不出。姐妹们相拥痛哭,父亲已哭不出眼泪,我只紧紧握了他的手,无语泪流。
很想再看看祖母,大姐把我带到祖母床前,我慢慢掀开低垂的帐子,把床单移开,眼前的祖母脸色如常,只不过闭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时夜晚看着她的样子。那时跟祖母一起睡,每晚要听着她讲古才能睡着。半夜醒来,我常常侧过头去看她,土布被上盖着祖母平日穿的大襟布衫,随她的呼吸起伏,她的嘴微微地张着。我静听那呼吸,有一会儿觉得呼吸好像停了,我便害怕起来,拿手轻摸一下她的脸,是暖和的,才把心放下。我常常想,袓母会不会死,早上要是叫不醒她该怎么办?
祖母常病,我这样的想法持续了许多年,直到我长大,直到祖母真的故去,可是她弥留的时候,最疼爱的孙女却不在身边。
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把手慢慢伸过去,用手背在她脸上轻轻滑了一下,冰凉冰凉的,不再是记忆中的温暖。
入殓的时候,我听到那“咔嗒”一声骨头的脆响,想起祖母的驼背,只觉山崩石落,心神俱裂,泪水一下子奔涌出来。
记得一位名人说过:悼亡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我们没有别的法子。知道死亡,和经历它,是不一样的。
是啊,痛失亲人的悲伤,没有经历过的,又怎能明白其残酷和无奈呢?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祖母离开我们已有廿载,永别之痛渐渐被时光掩埋至心的底层。然过往如昨,怀念依旧,那些最真的感情,最美的记忆,总是蔵在最深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