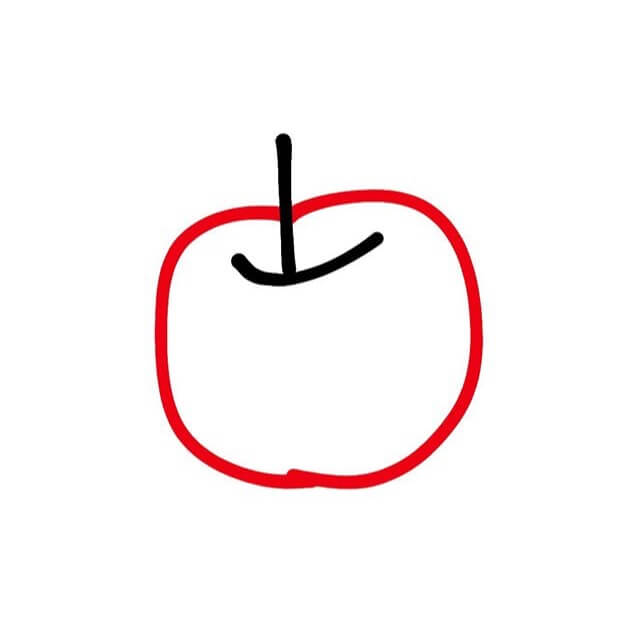清明祭
一场夜雨,将乡间田埂路上的泥泞冲洗得干干净净,季节的画师为远山近峦黛青的底色涂抹上一层抢眼的嫩绿,沁凉甜润的芬芳从初绽的枝芽间滴滴答答地溢出,浸入人的口鼻,弥漫在五脏六腑间。大红的杜鹃、雪白的梨花、金黄的油菜花在山坡上竞相开放,撩拨春风。春天,像一位情窦初开的村姑,在尽情地展示其勃发的生机。
坎坷曲折的山路上,祭祖的人们以家族为单元,三五成群、有说有笑走向先人安寝的坟场,全然没有“雨纷纷”陪伴下“欲断魂”般的悲戚,倒像是携家带口沐浴着明媚的春光去踏青、赏景。我心里在问:聪明的祖先们为何要将这满载着凝重、悲伤的祭祀安排在这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季节?
爷爷和父亲都英年早逝在同一个年龄段上,迷信的母亲为了避免悲剧的代际传承,在我没有超过爷爷和父亲阳寿的年龄,坚决阻止我上祖坟,待我在母亲的忐忑中活过了他们的阳寿,又就职在千里之外的省城,往返一趟需耗时三四天,忠孝不能两全,只有拜托离老家近一点的弟妹代我在祖坟上烧上几张纸,敬上几炷香。清明祭祖的场景只留在儿时模糊的记忆中。直到这两年有了清明小长假且高铁拉近了省城与老家的距离,才得以站在祖坟旁近距离直陈我的哀思!
老家的坟场错落排列着几十座坟茔,一座挨着一座,担心阴界的寂寞显然已是多余。可能是出于不同流派的风水先生对山形地脉的评判,抑或是后人对财富、人丁、仕宦的不同期盼,坟茔的方位取向显得有些凌乱,且大小有别,高矮各异,有的立了碑、圈了墓,有的只是一堆不起眼的小土丘,有的整洁光亮,有的杂草丛生,仿若一个未经规划设计由村民自由搭建的小村落。
儿时多次听奶奶说过,祖坟就像一棵大树,老祖宗是树根,然后长茎发枝,分杈分桠,逐渐根深茎壮、枝繁叶茂。我环顾坟场,目光定格在靠最里边那座用方石圈着的坟墓,我断定那是族人的根。抹去悠悠时光结下的存垢,在风雨剥蚀的碑面寻找历史的印记,模模糊糊中显出“嘉庆四年立”的文字。屈指算来,墓的主人已定居这里已近220年,以20年一代计算,这块墓地已是十代同堂。人过一百,形形色色,坟过一百,想必亦形形色色。每座坟茔肯定有一个区别于他人的生命故事,或悲或喜,或激越或舒缓,或精彩或平淡。
爷爷的故事是奶奶说给我听的,故事里充满了历史的诙谐。
我的曾祖父辈家境曾经殷实,置过良田数顷,雇过工,放过贷,在大家族中名望很高。然而,祖父因用鸦片治病而成瘾君子,祖上精打细算积攒的白花花银子源源不断填塞用鸦片挖掘的无底洞,积蓄花光了便当田卖屋。十几年间,数顷良田便在袅袅烟雾中化为乌有,爷爷的身份也在这烟雾中由雇主变成了佃户。乾坤轮回,因祸得福,新中国成立后按财产划定成分,一贫如洗的我家自然就划定为“苦大仇深”的贫农。在唯成分论的年代里,历史为我们家一路开放绿灯,以至我们少了几许命运的坎坷。
奶奶的故事是在奶奶的驼背上听到的,故事里满载着岁月的艰辛。
奶奶出生在湘黔交界处的一个小侗寨,3岁丧母,6岁因灾荒随父亲乞讨,被曾祖父用几块大洋收为童养媳,从此生命就烙上了刘家的印记。奶奶命苦,姑且不说一进刘家的门,家道就开始由盛转衰,直至一贫如洗,更为艰辛的是,正值中年爷爷就撒手西归,独自一人拉扯一双未成年的子女艰难度日。在我残存的记忆中,风烛残年的奶奶,弓着一副接近90度的腰,患着严重的哮喘,“呼嗤呼嗤”拉风箱般的,背上驮着我,手里牵着姐姐,呼唤鸡鸭、清扫庭院、浆洗衣衫。奶奶一生勤快节俭,忍辱负重,无怨无悔,在我们勤劳简朴的家风传承中,奶奶作出了特殊贡献!我在奶奶坟前默许,也教导年幼的儿子: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优良的家风不能变!
父亲的故事是在我的见证下演绎完的,故事里徘徊着幸与不幸的无奈。
父亲的幸,源于他的贫苦出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贫苦的农民成了社会的主人,父亲被挑选为土改工作队员,由于工作出色而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在老家,能够吃上皇粮是祖宗的造化,是家族的荣耀。即便后来弃官归田,他也长期在村里当村官,调解纠纷,明断是非,在十里八乡享有崇高的威望。父亲的不幸出自他不科学的生活方式。父亲对酒的钟爱难以用语言表达,一日无酒茶饭不香,三日无酒便萎靡不振,饭可以不吃,酒却不能不饮,及至后来身体出现毛病,酒与健康只能择其一,父亲竟然隐瞒病情一如既往地豪饮,英年早逝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父亲走向祖坟的那一天,我仰天长号:父亲啊,有什么嗜好值得用生命去捍卫呢!大智的你竟然铸成如此无法挽回的大错!
我满含热泪,斟上满满的三杯酒,祭洒在父亲的坟头,但愿他老人家能在极乐世界里慢酌慢饮,品味酒的真谛。
“轰、轰、轰”,祭祀的炮声回响在山谷间,树桠上鸟窝里刚出壳的小鸟“唧、唧”惊叫。郁郁葱葱的青草发出“吧、吧”的拔节声,春天在催生着万物,跪拜在祭坛前的儿子及小伙伴们稚嫩的气息与春天相映成趣,这蓬勃向上的景象足以让先人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