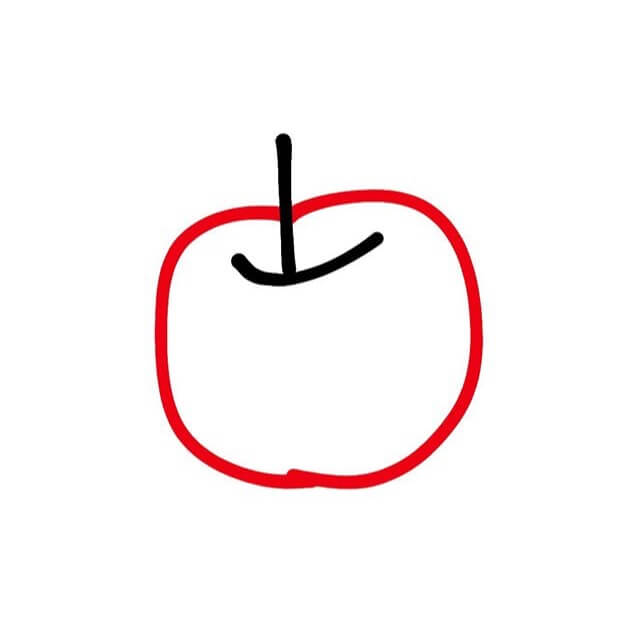悠闲不再
冬至,雨下得酣畅淋漓。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我窃喜地“滞留”家中,什么也不干,不可多得地闲逸着。
不知从哪一个年头开始,世界变得浮躁起来了,所有人都行色匆匆,疲于奔忙。人在着手这事,心还在惦念那事,劳劳碌碌,一刻也安闲不下来。
身心俱疲时,我不禁想念起旧时光来了。
那些年的农村,春种秋收之后,就开始进入悠然自在的冬闲了。女人们玩儿似地聚在村头路边,纳纳鞋底,织织毛衣,一边家长里短地开心海聊,放浪形骸的开心大笑声把太阳公公也勾得心痒痒,快快地爬上中天,当头腑瞰,想瞭望一眼女人世界的秘密。日将当午,女人们才各自星散,回家作炊备饭,叫老公儿女拢来午餐。勤快点儿的,背着背篓上山打把猪草,或者拾梱柴禾,或者浇浇菜园。园蔬不为市售,自给自足而已,所以,种得跟城里人养花草似的,养性怡情的样子,惬意而不紧张。
村夫们的冬闲时光就更其享受了。
闲汉们蹲在墙根下晒太阳,一支粗大的蛮竹水烟筒递过来递过去,轮番被汉子们环抱摩挲。抽烟的汉子从吊在烟筒半腰的烟盒里拈起一撮毛烟,用拇、食两指来回盘捻,轻柔而温情,感觉奇妙得很。揉捻了许久,捻成柔软浑圆的一粒儿,再细心地往烟筒上的黄铜烟嘴里填进去,拇指肚来回抚一抚,然后才优雅地拿起香头凑近烟锅,随即,嘴在上面的烟筒口不停地抽气,手拿着香火在下面烟筒腰腹部的“火口”上点烟。那香头点烟的动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用香头在烟锅上来回滚动揉抹,似乎调戏逗弄的样子,直到黄铜烟嘴里满满的丝状毛烟烧着焚化,才移开香头,嘴巴技巧性地往烟筒里突兀吹气,烟筒内的水突然受到气压,从拇指粗的烟嘴里喷射出来,把黄铜烟锅里的灰烬冲洗殆尽,汉子再抱牢三尺长的、溜光浑圆的蛮竹水烟筒猛地抽吸,把烟筒肚腹里满管的乳白色的烟雾吸进肺里,兜转萦绕一圈,再徐徐吐将出来。吸得把瘾了、美了,还情不自禁地发出极其享受的“嘶——哈”长音。
烟筒“哨子”都烧烫时,半早上过去了。有好饮者酒虫钻心,提议整两杯打发时光,众人一拍即合,沽酒拿碗搬桌子,就在光天地坝吼开了……
时光在欢乐之中很快滑向正午,婆娘们回去做好饭菜,来喊老公吃饭。汉子们吆五喝六,激战犹酣,正在兴头上,自顾酒场驰骋,哪管饭不饭?老婆也不恼,凑过来旁观,帮征战的老公把关,为之喝彩助兴。老公总输酒,递过来,也常常半推半就帮他喝两杯。老公的对手见酒往外出,也不计较,只是抬起醉眼瞟一眼那喝酒的婆娘,语气暧昧地打趣说:“喝嘛,喝得二昏二昏的,两口子大白天又约起……哈哈哈!”婆娘也不饶人,回敬对方道:“我家两口子到还可以那个呦,只怕你醉了像条死狗,你老婆咋个喊你都动不了呐!”嘻哈打笑间,欢乐的氛围弥漫了整个乡村的闲逸时空。
至于姑娘小伙们,有对象的,躲到隐密处你侬我侬,亲亲我我,如胶似漆;单着身的,则懒洋洋地在路旁的枯草厚绒绒的田埂上“看神仙过路”。逢到走过的是青春美少女,那眼睛呀,馋的跟什么似的!
……
时光在怡然自足与原始向往中悠然度过。那时的人不像现在这样“财心”重,“汲汲于富贵”。那时的世界也不如此这般让人浮躁不安和忧心忡忡。那些岁月,仿佛白云的脚步也总是慢慢吞吞,悠然自得的样子。
雨从冬至下起,三天都还没有放晴的意思。即使是最钟爱的雨天,即使什么也不用干,然而,这人闲着,心未必安闲。世事纷繁,俗虑伤神,焦躁盘桓,何得真正的安闲静心?
呵,真想放下功名利禄的无谓奢想,回到从前那样的慢时光,愿以后,全是从容悠然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