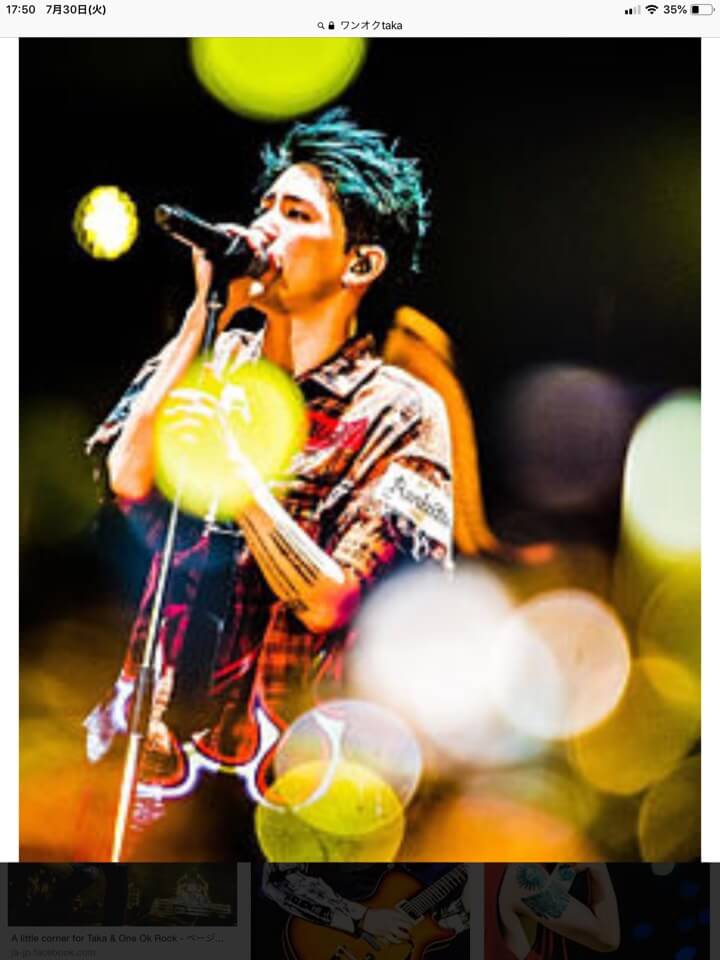相约奔赴“童年”
一
伙伴们召集,要进行一场奔赴“童年”的聚会。
童年,多么美好的时光。我们纷纷响应。到了坝墙子的时候,我屋院门大开,主人不在家,只有菜园几棵葱。不一会,老冬回来了。进屋先上热炕头,盘腿不大会了,伸着腿也不错。长得五大三粗的老冬,针线活却有一手。从前,她绣的八骏图,有人出价二万,她没卖,挂在家里了。这次她再绣“八骏图”,是给荣梅的。她绣的马,红的好像一朵盛开的木棉花,白的像天上的云朵,绿草地像苍茫大草原。
我们坐在炕上嗑瓜子,聊天,嘴里含着高粱饴糖嗑瓜子,是小时候最幸福的事。香瓜掰三瓣,像从前一样。卡拉OK机搬出来,屋子成了“歌厅”,红双唱“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我唱“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荣梅唱“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梦中的繁华”…
正唱的热闹,老姐夫端着一盆热腾腾的米饭从大门外回来了,白花花的米饭上一层锅巴外焦里嫩散发诱人的米香,米饭是大嫂子家灶上大铁锅里焖的,玉米杆作柴火,煲出一锅“饭锅巴”!“锅巴”是我们的最爱,那里有童年的味道。在厨房里帮忙的李伟,见了锅巴过来掰走了大半。余下的被我、凤梅、荣梅、红双给吃的只剩一点点,那“一点点”还是特意给没到的留的!说话间,玉玲、金枝也到了,红双给她们俩一人一个热烈的拥抱。外屋的忙着准备吃喝,里屋的坐在炕上心花怒放。凤梅是个勤快人,来了就在厨房帮忙。摘豆角、摆桌子,蒸虾爬、酱海螺,不一会一大桌子菜就齐活了。
乡村的傍晚,晚霞如一条绯红色的纱巾,围在日落的天际。柔蓝色云彩层层叠叠,电线上落的鸟都已归巢,老屋门前的灯火映着小院,光束下广桥的背影一点点的走进去,穿过推拉门,等待他的是一桌子的欢腾,一桌子的过往,一桌子的发小情深。在这故乡老屋,我们围坐在一起打开童年的宝盒。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9点,老冬说,都不走了,今晚都住下。说着她伸手打开柜子,里面一大摞棉被、枕头,喜鹊蹬枝,百鸟朝凤。她说,够你们铺的盖的。我们都不走了。三间房,二铺炕,住下十多个发小。坐在热炕上唱歌,卡拉OK机蓝色屏幕上,绿色音频跳跃着,如同一条在水里嬉戏的鱼。
二
在歌声中,我想起1977年夏天,在六队部平房朝西一间小屋“育红班”一溜小板凳上,坐着6岁的我和红双、玉凤、7岁的荣梅、凤梅,8岁的老冬,一块小黑板,老师用粉笔写“一 二 土”。一起跟着老师学着用“蒿草”做扫把,一起在史家小学的操场上跳皮筋。一起打探放映电影的消息。当得知晚上在六队场院里演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占席位”,我们跑到村东头的小树林,捡来小树枝,一根树枝折成几段,插进场院的地面,圈出一小块四四方方的地界,抱来一小堆碎稻草,完整的稻草杆是不能随便用的,完整的稻草要用来搓草绳、打草袋。我们把稻烂子铺到方格子木棒圈起来的地方,上面铺上一张塑料布,松软又整洁。晚上,母亲们盘腿坐在上面,抽着旱烟,低声议论着屏幕上的女人。我们坐在母亲身旁,盯着那块被风鼓起的幕布,心里都是满足的快乐,和周围伸着脑袋从缝隙里看电影的站着的人群相比,我们的“观影席”实在太过高级。
1984年我们一起上了中学。放学的时候走在从新开农场通往史家村那条蜿蜒且漫长的路,有时我们会惊喜的看到光波大舅赶着马车从远方飞驰而来,只见他勒紧缰绳,喊出了那一声我们无比期盼的“吁…”马车停下来,光波大舅一声招呼,“上来吧”!就好似马车上有宝贝一般,我们撒欢的爬上大马车,光波大舅再来那一嗓子“驾!”大红马得了令,开始奔跑起来,黑色的马鬃甩来甩去,矫健有力的后腿无比健美的飞奔。我们坐在马车上晃荡腿儿,一起数着路边的电线杆一根一根的向身后退去,史家村袅袅升起的炊烟渐渐近了…
去中学要经过火车站那两趟铁轨。那时候没有高架桥,也没有桥洞。只有穿过铁轨才能通过。那常常停着火车,拖着无数节车厢,把个路堵住,我们过去的唯一方式,是从跳上两节车厢链接处,再从上面跳下来,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而我向来不灵活,上体育课的时候,伙伴们身轻如燕,助跑、双手在跳箱上用力一撑,一个漂亮“飞燕”式,就完成了跳鞍马,而我总是在每次助跑后趴在箱子上以失败告终。每次对付有火车的路口,我总是被伙伴们或是推举,或者拉着,才过得去,总是胆战心惊。
三
“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老冬甜甜的唱着,她坐在炕沿上,一手举着手机看着字幕,一手打着拍子。随着节拍舞动着浑圆的身子,好像摇摆的企鹅。我搂着老冬的脖子,趴在她厚实温暖的背上,就像小时候她背着我走在故乡的田埂上。
夜里,我们再次围坐在饭桌前。下午炖了一条大鱼---十五斤重的胖头鱼,在大灶上,经过煎、焖、煮,配上自家大缸酿的豆瓣酱,灶坑里玉米杆燃的通红的火炖煮个把钟头,一锅味道鲜美的铁锅炖鱼俘获了所有人的肠胃。鱼汤蘸苦麻菜,一种特别的味道。苦麻菜是老冬早上顶着小雨在田间地头剜回来的。
夜晚睡下,西屋炕上从东向西依次躺着玉凤、荣梅、我、红双、金枝、玉玲。地上沙发上躺着老冬。六个女生并排躺在一起,三个人盖一床棉被,就像小时候一样。夜晚,我听见身边的荣梅发出均匀的呼声,红双、金枝也都进入梦乡。我披着衣服走出来,站在院子里,三间老屋,门廊的光束从窗口透出来。李子树包裹着一层白色的花朵,在夜色里吐露暗香。夜晚的天空,亮着两颗星。一弯月牙无比明亮的镶嵌在黑夜的幕布上,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诗意的析居》里写道:群山无言地庄重,岩石原始地坚硬,杉树缓慢精心地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而又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原肃穆的单一——所有的这些风物变幻,都穿透日常存在,在这里突现出来,不是在“审美的”沉浸或人为勉强的移情发生的时候,而仅仅在人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之际 严冬的深夜里,风雪在小屋外肆虐,白雪覆盖了一切,.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思考呢?而深夜站在故乡的院落的我,此时成为一个精神世界诗意栖息者。在寂静的星空下,我感受到一种久远时空传递而来的记忆密码,它分分秒秒倾泻而出。失去的一切瞬间复活,童年的一切都仿若重新来过,年少的伙伴,正青春的哥姐,人到中年的父母,在故乡狭长小路上那辆被我们推出来的哗啦啦山响的老旧自行车,还有日暮时分母亲站在家门前的一声声呼唤…在不知不觉中沿着岁月的中轴线行进的我们,在有涯的生命里经历、感知、打磨,我们的外在不断的变化,长大、长高、脱去稚嫩,我们学着用双肩扛起一些什么,我们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去表达,在串联起来的时空印记中,我们看到了在路上奔跑的自己,我们欣慰于被爱,能去爱,被给予,能够给予。我们坦然接受岁月馈赠给我们眼角的第一道皱纹,我们学会理解生命的加减法则,日渐强大丰富的内心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安宁且富足。
深夜的村庄已经睡去,树木都隐藏在黑暗当中。我伸手拉开推拉门,脱去鞋子,侧身躺在荣梅与红双之间,很快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起,老冬给赶上生日的我准备了6个红皮煮鸡蛋,要我把鸡蛋在炕上滚滚,在身上滚滚,意在好运来。我都照着做了,鸡蛋在炕上滚过,在胳膊上滚过,充满了仪式感。
走出老屋的时候,朝阳将小院撒上一层金子般的光芒,李子花在湛蓝的天幕下绽放。大家准备离开了。在这个夜晚,我睡了一晚热炕,看到了好久都没看到的最亮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