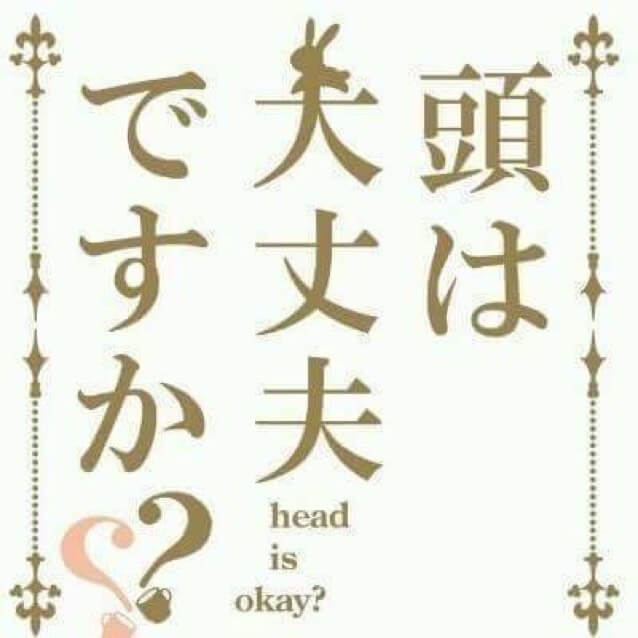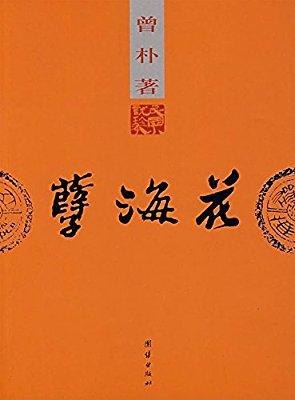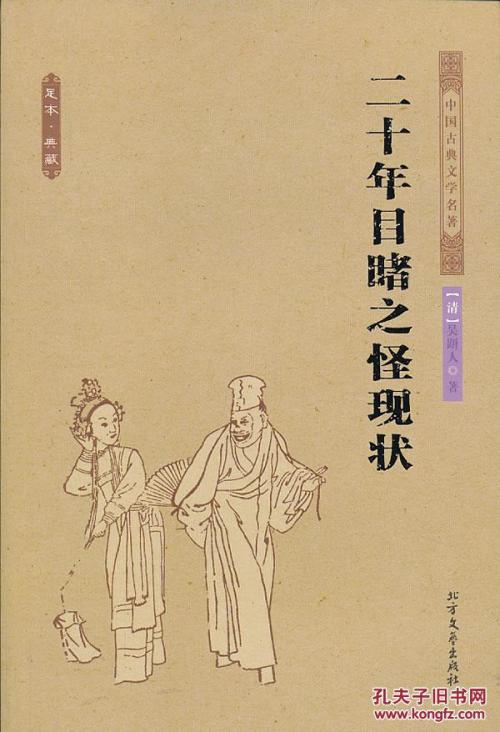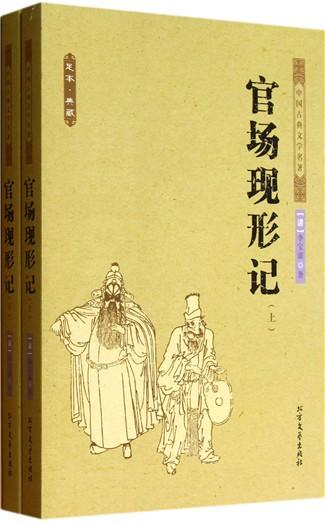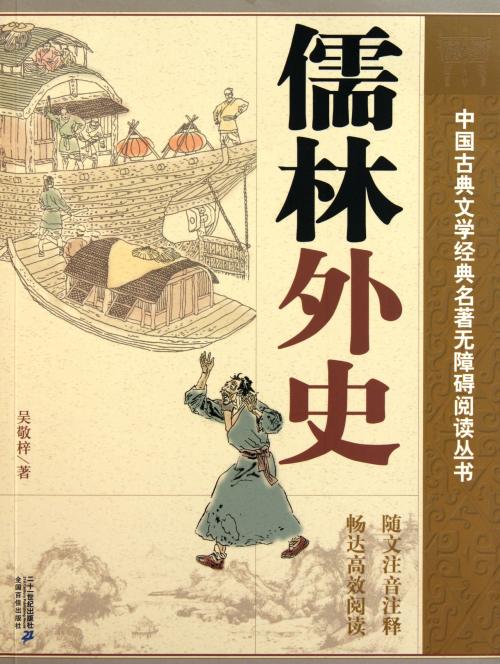读后感
这本书能成为大众文学常识的一部分,还得归功于英明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二语文课本“明湖居听书”一课,其中黑妞白妞的唱功如“钢丝”般抛入天际、回环曲折的描写,相信曾经的语文课代表们定然记忆犹深。
通读全书,你会惊叹刘鹗对于自己作品体裁定位的洒脱与随意。正篇加续集短短二十九回,小说的身份屡屡变换。一个世纪前的刘鹗仿佛和一个世纪后的文学评论家们较上了劲:你说我是世情小说,我偏给你来个断案;你刚把我划进公案小说,我这里奇峰陡起,再掺和点神怪色彩;你要开始讲神魔小说,我又谈情说爱起来……一套迷踪拳从头忽悠到底。
起首叙述老残一梦,见海上一船将沉,水手在那里趁火打劫,抢夺乘客财物。有一种人又高谈阔论演说,煽动船上人反抗,结果“不过用几句文明的话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老残去献罗盘救人,反被诬为汉奸,只好落荒而逃。这种谴责小说笔法,状物要影射时局,故而倘恍迷离 ,未辨梦醒,乃当时几十年间文坛惯用的手段。鲁迅写《狂人日记》,满纸“吃人”,寓意游走在梦幻与现实之间,也深得此法神髓。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老残游记》“叙景状物,时有可观”,可见得他是仔细观过的。
第八回写申子平上桃花山访刘仁甫,月夜遇虎,魂不附体。好容易在荒山找到个人家,开门是个须发苍然的老翁。说要借宿一晚。“那老翁点点头,道:‘你等一刻,我去问我们姑娘去。’说着,门也不关,便进里面去了。子平看了,心下十分诧异:‘难道这家人家竟无家主吗?何以去问姑娘,难道是个女孩儿当家吗?’既而想道:‘错了,错了。想必这家是个老太太做主。这个老者想必是他的侄儿。姑娘者,姑母之 谓也。理路甚是,一定不会错了。’”这个悬念后隔了三段,这位“姑娘”出场,却是位妙龄奇女子,名唤涂玙。这段暗藏玄机,笔法兔起鹘落,而五十四年后的《笑傲江湖》如此叙述任盈盈出场:“正要转身再入竹丛,忽听得绿竹翁叫道:‘姑姑,怎么你出来了?’王元霸低声问道:‘绿竹翁多大年纪?’易师爷道:‘七十几岁,快八十了罢!’众人心想:‘一个八十老翁居然还有姑姑,这位老婆婆怕没一百多岁?’”两段描写显系一派家数,金庸的书架上恐怕也端坐着个老残。
此书在《绣像周刊》发表时,平江 不肖生年方弱冠,环珠楼主刚满周岁,王度庐远未投入娘胎,而刘鹗已深得武侠小说笔法虚实相生的三昧。写申子平遇黄龙子和涂玙,难辨两人是人是仙,便为一例:
子平道:“……尊大人是做何处的官,在何处值日?”女子道:“……家父在碧霞宫上值,五日一班。合计半月在家,半月在宫。”
子平听说大喜,说道:“今日得遇诸仙,三生有幸。请教上仙诞降之辰,还是在唐在宋?”黄龙子又大笑道:“何以知之?”答:“尊作明说‘回首沧桑五百年’,可知断不止五六百岁了。”黄龙子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此鄙人之游戏笔墨耳。公直当《桃花源记》读可矣。”
子平……即问道:“先生,这是什么?”笑答道:“骊龙之珠,你不认得吗?”问:“骊珠怎样会热呢?”答:“这是火龙所吐的珠,自然热的。”子平说:“火龙珠那得如此一样大的一对呢?虽说是火龙,难道永远这们热么?”笑答道:“然则我说的话,先生有不信的意思了。既不信,我就把这热的道理开给你看。”说着,便向那夜明珠的旁边有个小铜鼻子一拔,那珠子便像一扇门似的张开来了。原来是个珠壳,里面是很深的油池,当中用棉花线卷的个灯心,外面用千层纸做的个灯筩,上面有个小烟囱,从壁子上出去,上头有许多的黑烟,同洋灯的道理一样,却不及洋灯精致,所以不免有黑烟上去,看过也就笑了。
这三段先扬后抑(anticlimax),回旋跌宕,真有点王小玉说书的意思,而最后读者仍然人仙莫判。涂玙所言碧霞宫,既可能是个山中的小道观,也说不定是天上宫阙(道教有碧霞元君);黄龙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或为真言,或为托辞;而骊珠的神话色彩破灭,也无法证伪或证实二人的身份。答案扑朔迷离 ,整书始末,都无从揭晓(opentointerpretation)。文学教授们讲解中国古典小说的现代特征,或该考虑从刘鹗开始。
而接下去黄龙子议论时事一番高论,杂糅科学、神话、政治、术数,自成格局,更令读者瞠目结舌。他先从月球半明半暗的道理入手,普及了恒星、行星、卫星的基本天文学知识。遽而又跳入了“北拳南革”和“三元甲子”:
黄龙子道:“……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此一个甲子与以前三个甲子不同,此名为转关甲子。此甲子,六十年中要将以前的事全行改变:同治十三年,甲戌,为第一变;光绪十年,甲申,为第二变;甲午,为第三变;甲辰,为第四变;甲寅,为第五变:五变之后,诸事俱定。”
子平道:“前三甲的变动,不才大概也都见过了:大约甲戌穆宗毅皇帝上升,大局为之一变:甲申为法兰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役,大局又为之一变;甲午为日本侵我东三省,俄、德出为调停,借收渔翁之利,大局又为之一变:此都已知道了。请问后三甲的变动如何?”
黄龙子道:“这就是北拳南革了。北拳之乱,起于戍子,成于甲午,至庚子,子午一冲而爆发,其兴也勃然,其灭也忽然……主义为压汉。南革之乱,起于戊戌,成于甲辰,至庚戌,辰戌一冲而爆发,然其兴也渐进,其灭也潜消……主义为逐满。此二乱党 ,皆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也。北拳之乱,所以渐渐逼十出甲辰之变法;南革之乱,所以逼十出甲寅之变法。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销灭。魏真人《参同契》所说,‘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属土,万物生于土,故甲辰以后为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坼甲,如笋之解箨。其实,满目所见者皆木甲竹箨也,而真苞已隐藏其中矣。十年之间,锋甲渐解,至甲寅而齐。寅属木,为花萼之象。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虽灿烂可观,尚不足与他国齐趋并驾。直至甲子,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进于大同之世矣。然此事尚远,非三五十年事也。”
这是政治(且不论正确性),也是堪舆。1874年(甲戌)同治驾崩,1884年(甲申)中法福建马尾海战,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甲辰)华兴会成立、长沙起义,这四十年往事都落入黄龙子的天干地支小算盘中,而之后的只属预言。刘鹗的归纳法还算精彩,演绎法却大谬不然。1914年(甲寅)非但没有变法,孙中山还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 。而1924年(甲子)之时,中国再无一个皇帝,遑论“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了。当然这些刘鹗都无从亲见,1908年(戊申)他因“私售仓粟”罪被清廷流放新疆,1909年(己酉)死于乌鲁木齐。哈雷预言彗星将至,他死后十六载彗星果至,刘鹗与其相较,当加额庆幸于九泉。
论到这里,黄龙子意犹未足,又说上帝并非唯一尊神,常与阿修罗争战。而势力尊者更凌驾于两者之上:
我先讲这个“势力尊者”,即主持太陽宫者是也。环绕太陽之行星皆凭这个太陽为主动力。由此可知,凡属这个太陽部下的势力总是一样,无有分别。又因这感动力所及之处与那本地的应动力相交 ,生出种种变相,莫可纪述。……
1859年李善兰将牛顿的《谈天》译入中文,从此中国人知道了万有引力定律。刘鹗轻描淡写地将科学和神话撮合,于是牛顿和势力尊者这两个素未谋面的意象并排站在了读者目前,不过这也非国人原创,几百年前但丁的世界中,托勒密和上帝不仅相安无事,而且亲密无间。在《神曲·天堂篇》第十歌中,但丁描述黄道和赤道角度不偏不倚,若增一分减一分,世间生灵都会毁灭,而这正是上帝之力使然。地球是圆的并不妨碍上帝坐在上面,正如万有引力反倒可以为“势力尊者”张本。在文学家的喜宴上,科学和宗教或神话常常把酒言欢,不醉不归。
刘鹗和但丁的缘法不止于此。《老残游记续集》最后三回叙老残游地狱,调子又转为神魔小说,而形状陰间种种酷刑,与《神曲·地狱篇》也大可比观:
只见两旁凡拿骨朵锤、狼牙棒的一齐下手乱打,如同雨点一般。……起初几下子,打得那大汉脚直竖上去,两脚朝天,因为辫子拴在木桩上,所以头离不了地,身子却四面乱摔,降上去,落下来,降上去,落下来。……落下来的时候,那狼牙棒乱打,看那两丈围圆地方,血肉纷纷落下,如下血肉的雹子一样;中间夹着破衣片子,像蝴蝶一样的飘。皮肉分两沉重,落得快,衣服片分两轻,落的慢,看着十分可惨。
磨子上的阿旁接住了人、就头朝下把人往磨眼里一填,两三转就看不见了。底下的阿旁再摔一个上去。只见磨子旁边血肉同酱一样往下流注,当中一星星白的是骨头粉子。
这是刘鹗的“打”字诀和“磨”字诀,我们再来看看但丁的“裂”字诀:
一个酒桶即使失掉了中板或侧板,
也不如我所见的一个人那破损不堪,
那人竟被劈成两半:从下巴一直劈带屁眼:
大小肠悬挂在两腿只间,
心肺肝脾全都暴露在外面,
……
我始终觉得西方暴力美学的鼻祖是但丁,当然刘鹗也不遑多让,在中国酷刑大观中能坐上把交 椅。“叙景状物,时有可观”,放在这个具体语境下,不知是褒是贬。当然两人的主旨倒都还是惩恶劝善。《续集》中叙老残心理活动:“倘若我得回陽,我倒愿意广对人说。”但丁也受了好多陰魂嘱托,让他们以己为诫,莫要犯错堕落,毕竟下了西方地狱,是要把一切希望捐弃,永世不得超生的,而老残这里,还能依罪恶多少,定被“磨”的次数,再磨蹭也有个盼头。
以上所举谴责、武侠、堪舆、神魔,仅四大端而已,其余如叙贾氏一家离奇命案的公案小说,叙泰山斗姥宫尼姑逸云恋爱的心理小说,以及其后逸云大彻大悟的修真小说,琳琅缤纷,不一而足。倘若刘鹗能将这些类型以严整的情节结构表现出来,那他在文学榜上的座次恐怕能压过曹雪芹。只可惜他是时而武侠、时而神魔、时而谴责、时而公案,一部小说好似选集,彼此未能熔融无间。张炎评吴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刘鹗正好相反,好比秦砖汉瓦,唐彩宋雕,分别看来,动人心魄,搭在一起,不合体统。当然,清季古典小说余绪中,《老残游记》的头名状元还是能做稳的。
刘鹗文字功力上乘,对书名却未免太过随意。叫做《老残演义》固然不太妙,和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拼起来,它怎么也挤不进中国古典小说的一流行列。但若改为《中国类型小说大观》,那么这个领域,他刘鹗可算妙人一个,泰斗半双,独步古今,享誉全球。结果却搞了个《老残游记》,岂不让徐霞客偷笑?
可见名字一事,到底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