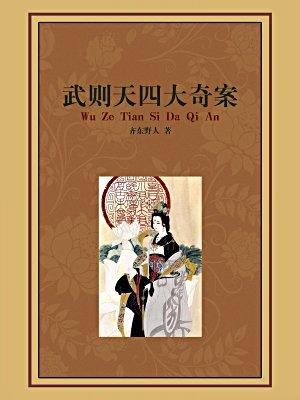第三十二回 杜大隆娶媳得女 徐二混因贪破财
却说墨意师见徐有财供出两回都是他的原媒,料想推辞不过,只得实说道:“大老爷听禀,并非小的敢装糊涂,因徐二混与黄三林本是磕头弟兄,他俩面对面的结亲,不过叫小的做个现成媒人。后来黄三林故了,前年徐二混对我说黄家的亲事退了,小的也不知他怎么个退的。可巧杜二掌柜二儿断了弦,托小的做媒,小的就想起徐二混这一门亲了,不想一拍便合。这也是前生缘定,与小的无干。这所供的都是实话,求大老爷详察。”李公道:“胡说!”
正要再问,值日差禀黄三林妻子黄倪氏、黄祖永传到。李公叫到案前,问道:“黄倪氏,你儿子聘徐可忠的女儿,是谁的媒人?”倪氏道:“是张保田同这位墨大爷。”李公道:“张保田现住在哪里?”倪氏道:“听说今年夏天已病故了。”
李公道:“聘礼共是多少?有首饰衣服没有””倪氏道:“聘礼银四十两,是四个小宝。首饰是赤金耳环一副,赤金扁簪一支,包金手镯一双,包金如意簪一支,白银手镯一双,白银髻花一支,白银耳环一副,白银冠钻一支,共是八件。另外,尺头四个,就是没有衣服。”李公说:“据徐有财供,聘礼已经退回,你可照数收到没有?”倪氏道:“我的青天老爷呀,小妇人哪里收回一件?就只凭徐亲家说,将聘礼折卖还了账了。小妇人也不知是谁的账。”李公道:“庚书婚帖退回没有?”
倪氏道:“庚书婚帖,小妇人一齐收着,并没退回。”李公道:“将婚书庚帖呈案。”倪氏道:“现收藏在家。”回家叫鹿儿赶快取来。这一回头,方才瞥见上首坐的就是昨天喝茶的那位客人,真是又惊又喜。正想再诉赖婚情形,却遇值日差带徐可忠到案销差。
李公问:“你是徐可忠么?”答道:是。”李公道:“你是不是又叫徐二混?”二混面赤,低下头不敢答应。李公道:“你女儿既聘给黄三林的儿子黄祖永,怎么又嫁姓杜的?一女两聘,是何道理?快快说来。”徐二混明知理短,只得勉强分辩,禀道:“因为黄亲家故,家道渐渐的不济。”李公道:“家道不济,你便应该赖婚?”徐二混叩头道:“不敢。只因黄亲家在日托小的转借头谷钱二百五十吊,前后五六年,分文未还,合计本利已五百多吊。小的又无力代还,只得与亲家母商议,将聘礼退回,折变了还帐。小的想,聘礼已经退回,这亲事就不能算了,所以将女儿另聘,并非赖婚。求大老爷明鉴。”
李公问倪氏道:“你亲家说聘礼退回折变,交 给你手没有?”
倪氏道:“小妇人并没看见。”李公喝道:“徐可忠,你敢在本县面前说谎!你既说退回聘礼,怎的黄倪氏没有收回?你是亲手退回的,还是交 原媒退回的?有个证据没有?”徐二混听了这话,愣了半晌,方说道:“因为当日债主逼得紧,容不得空,因此向亲家母说明了,就立刻变价清帐,容不得再来回来去的耽误工夫。这是实情,亲家母都知道的。”李公道:“你这嘴也很会说。就依你讲,这聘礼已只算得变卖了,算不得退回;何况还有婚书、庚帖明明的在姓黄的手中,你想将女儿另嫁姓杜的,这个理,凭你利口只怕不容得你讲。”便顾左右道:“来,速传杜大隆回话。”值差的答应着飞跑的去了。暂且按下。
列位听说徐二混既打算赖婚,岂肯不把婚书、庚帖设法要回,还叫留在黄家做打官司的证么?这又是编书的胡 造谣言。
哪知非也,其中有个缘故。一来徐二混与黄三林结亲并非真心愿意,原不过借这亲家的名目骗黄三林的财产。偏偏黄三林是个没心眼儿的人,居然被他骗上,钱财房产已经完了,又找补了一条性命。徐二混功行圆满,心安意足,这儿女姻亲哪里还在他心上?所以挖空心思,还要捏造这五百多吊钱的帐,原为得消除这四十两聘礼并八件金银首饰起见。倘没有这许多东西,他也便绝口不提的了。至于婚书、庚帖,在徐二混原没有算做凭据,只当是黄三林的勾魂票,料想孤儿寡妇 ,断没这力量与他计较。所以坦然放心,把女儿重又出聘。不想怨重毒深,黄三林死不瞑目,九泉之下起而控诉。又遇见这位不惮烦劳的李明府,单为了这事亲身查访到此。这不但徐二混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就是李公在签押房做梦的时候,也想不到这事是这样迅疾。且再想不到徐二混早留下这一套婚书、庚帖,为他听断的证据。这也叫害人自害,天夺其魄。并非说闲话打岔,这其中情节不得不交代一番。
且赶紧再说黄祖永,听他母亲叫他回家取婚书,他爬起来就走。赶到家里,将婚书、庚帖,两个龙凤泥金的套帖连拜盒一起,一直捧到双顺居跪下,交 与他母亲看了,呈上公案。李公接过,打开一看,便举在手中,问徐二混道:“这是你女儿的庚帖不是?”徐二混面红耳赤,不敢再辩,只得低着头说道:“是。”李公道:“既然是,你该怎么办?”徐二混还没有回答,差人已带杜大隆到案,衣冠齐楚的朝上跪下。李公问道:“你是杜大隆?”答道:“是。”李公道:“你娶儿媳也该探听探听明白。徐可忠的闺女已许黄祖永为妻,庚帖现在,怎么你敢设谋诓娶有夫之女?今本县已传齐两造,讯明原委,供证确凿,本应照例严办,姑念你两家也是体面人家,都被媒人所误,且传你来当堂商酌,这件事该怎样个了法?”杜大隆道:“老父台明鉴,职员实系不知徐黄两家的原委。蒙老父台讯明,免职员误娶有夫之女,为此感恩不浅。还求老父台格外成全,职员无不听命。”李公道:“听你这话,倒明白的很。你既称职员,这国家的法律你自然该知道的。且问你,一女两聘该怎么办?娶有夫之女该怎么办?”杜大隆道:“职员乡愚无知,蒙老父台教训,还求宽典,法外施恩,成全职员脸面。”李公道:“你既这样说,要照例办,你是知道的了。你既求宽典,本县俯准你的意思,准你两家量力罚钱,你愿意不愿意?”杜大隆道:“蒙老父台成全,职员无不从命。”李公道:“你既愿意,可暂且下去,赶快与徐可忠商议,问他也愿意否罚。既办,本县一秉大公,因格外从宽,听你们自己酌量。”徐二混叩头道:“求大老爷开恩,小的愿意受罚。”李公道:“既你们愿意认罚,听本县判断。”唤左右,传轿内的新人上来。
哪知道杜大隆的儿子本是一团 高兴的迎新,万想不到出这意外的岔儿。在轿内坐着纳闷,看风色不好,又被那看热闹的人七嘴八舌,你言我语,越加不好意思,敞着轿帘又没个躲闪,只好撩开扶手,抱着头,一溜烟的跑回家去了。单剩个新娘在轿内呜呜的哭。值日差叫喜娘打开轿帘,把新娘扶出,搀到公案前,揭去盖头。李公望下一看,虽然是庄家闺女,却倒长得骨肉停匀,五官端正。又加装扮得齐齐整整,珠冠霞帔,玉带蟒袍,越显得精神丰采。就是两个眼哭得红肿,像核桃一般。
迨把盖头的彩袱揭去,看见黄倪氏跪在右边,他便直扑下去,倒在倪氏怀里,放声大哭。倪氏也两泪交 流。李公不禁连连的点头,说道:“姑娘,这是你百年的大喜,不可如此。你的意思,本县已明白了,可惜你的父母不能体贴你苦心。待本县给你做主。”那姑娘听这位大老爷的话正碰在心坎儿上,越发感动,哭个不止。黄倪氏好容易将他止住了哭。李公问徐二混道:“你女儿这情形看见没有?非遇见本县,只怕你女儿性命还被你断送了。”二混叩头道:“大老爷恩典。”李公叫招房将各人前后口供念了一遍,给大众听了,说道:“这亲事,黄祖永自幼聘定,媒证、庚帖现在。徐可忠贪利无耻,一女两嫁。杜大隆为儿娶妇,贪得厚奁,诓娶有夫之女,都该照例严办。姑念自知理短,情愿受罚。今两家各罚地二百亩给黄祖永管业,以偿其含冤莫诉之苦。着即各将地亩指明界限,交 户房当堂立案。”徐、杜二人没法,只得各指拨了二百亩地,户房照录了地段、坐落、方向,俟结案后再行过割。李公道:“本县格外体恤黄家孤寡无力猝办迎娶,杜大隆枉费辛苦,一旦人财两空,也觉少兴。今为你设法周旋:徐可忠女儿可就此行礼,认杜大隆为义父;杜大隆预备为儿子续弦的喜筵,即借为替义女招赘的花烛;徐可忠陪嫁的装奁,既已送往杜家,可以毋庸取回,黄祖永就杜家成亲,认为义岳。从此三家一样姻亲,和气往来,莫存意见。本县这样调处,你大众愿意罢?”众人齐声禀复遵断,而黄倪氏母子喜出望外,尤为感激涕零。
李公又叫地保王顺到案说道:“你为地保,地方有不合理的事,应该禀报本县知道。你不但不来禀报,反去替他们帮忙,就该重责。今一概免究,着这事照本县的判断办去,倘有不合,惟你是问。”地保答应;“喳。”请了个安,正要下去,李公道:“且慢。本街东头第二堡的更夫,成群聚赌误公,应与重责。本县看此地道旁官沟壅塞,着你查明昨儿聚赌的四个人,各罚他十天工作开沟。待诸事齐毕,你一并销差。”地保一一答应,退下,遵谕办理去了。
杜大隆上前禀道:“蒙老父台公断,职员感激不荆但是职员尚有个下情:徐氏断归黄家,理所应该,但职员为儿子原定的聘礼,还求老父台追还。”李公道:“你聘礼多少?”杜大隆道:“纹银一百两,首饰八件,衣服四套,还有鹅、酒、糕、果、茶叶等项在外。”李公道:“这聘礼是应该追的。但追回来也是没你的份了,照例应该入官。姑念你伤耗已多,着将银两充义学公费,衣服首饰概行赏还。”徐二混道:“银两小的愿还。衣服、首饰已全数给女儿陪嫁了,求大老爷明鉴。”
黄倪氏禀道:“既徐亲家已将衣饰陪嫁,是杜家的聘礼,自然不该留下。待媳妇过门,应当照数拣还。”李公道:“很好。你各人都具上结来,完案后好赶快成亲,无误吉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万事不由人算计,巧谋豪夺更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