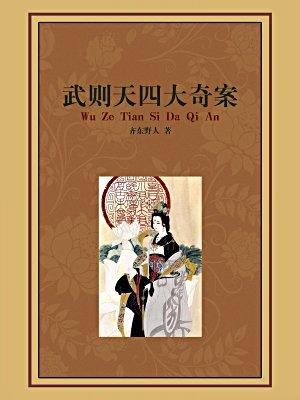《明儒学案》发凡
从来理学之书,前有周海门《圣学宗传》,近有孙锺元《理学宗传》,诸儒之说颇备。然陶石篑《与焦弱侯书》云:“海门意谓身居山泽,见闻狭陋,常愿博求文献,广所未备,非敢便称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门主张襌学,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锺元杂收,不复甄别,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也。学者观羲是书,而后知两家之疎略。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於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於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程、朱之闢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际,使无遁影。陶石篑亦曰:“若以见解论,当代诸公尽有高过者。”与羲言不期而合。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
儒者之学,不同释氏之五宗,必要贯串到青原、南嶽。夫子既焉不学,濂溪无待而兴,象山不闻所受,然其间程、朱之至何、王、金、许,数百年之后,犹用高、曾之规矩,非如释氏之附会源流而已。故此编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着者,总列诸儒之案。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於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胡 季随从学晦翁,晦翁使读《孟子》。他日问季随:“至於心,独无所同,然乎?”季随以所见解,晦翁以为非,且谓其读书鹵莽不思。季随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学者,其不轻授如此,盖欲其自得之也。即释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景玩弄耳。此书未免风光狼籍,学者徒增见解,不作切实工夫,则羲反以此书得罪於天下后世矣。
是书搜罗颇广,然一人之闻见有限,尚容陆续访求。即羲所见而复失去者,如朱布衣《语录》、韩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斋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内有斯文之责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
姚江 黄宗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