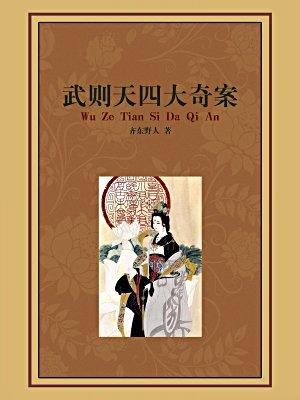黄金案-第十三章
马荣、乔泰兴高采烈赶回“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在独酌,卜凯则已醉伏在桌上,呼呼打鼾。
金昌揖礼道:“你两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与玉珠商定,今夜她答允陪我们去逛番仁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哩。”
乔泰听说今夜能逛逛番仁里,正好开个眼界。狄公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的。又听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将卜凯摇醒,不由他分说,与马荣两个一边架起一条胳膊,搀扶着随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渡口。
小舟很快划到花船前,玉珠果然盛妆描抹了,立在船栏边等候。
乔泰深情地痴望着她,她也朝乔泰微微一笑:“你两位怎的也来了?”
乔泰小道声,“这两日正想死你呢。”
四人上来花船。乔泰暗里捉了玉珠的手腕又问:“玉珠小姐今夜陪我们去玩番仁里?听说那里花样新鲜,五光十色。”
玉珠淡淡一笑:“你先来我房中坐了,我有话与你说。”
乔泰点头,跟随玉珠下了后舱。玉珠沏了一盅香茶捧上,两个正亲昵说着话。金昌进来道:“乔大哥,马大哥上面唤你去哩。”
乔泰不悦,心中虽留恋着玉珠,,又不知马荣叫他有何事,只得硬着头皮上来船面。
且说马荣与卜凯正在船头赏玩,金昌则去与鸨母赔话,卜凯道:“马荣弟,我与你去船尾看看如何?”
马荣道:“船尾堆屯若货物,又有有什么好看的。”
卜凯一手牵了马荣,便往后面船尾方向走。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荣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头,屏息不吱声。
卜凯大声笑道:“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云日犹余一线彩弧,海水幽蓝,明星照耀,正是人境难得的奇景。”
马荣看了半晌,并不甚觉有趣,便绕过船尾欲回去前舱找别的女子,忽瞥见铁锚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正与他们在小菩提寺后殿神龛下见到的一模一样,心中不由狐疑。正踌躇间却见乔泰寻路而来。
“马荣弟,叫我来有何事?”
“你且看这些根禅杖,这花船上如何也有这劳什子?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寻欢 作乐哩。”
乔泰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觉可疑。
“马荣弟,我们须留个心,暗中查访,倘是真撞着有和尚,定不轻饶。”
“咦,乔泰哥,你如何不去陪侍玉珠小姐?”
“不是你唤我来的么?”乔泰不无埋怨。“就来看这堆破禅杖!”
马荣这时乃发觉卜凯不知到哪里去了,忙问:“谁叫你来的?”
“金昌来传的话,说是你唤我。”
马荣叫道:“上他两个当了!你快下舱去责问金昌,我这里寻着卜凯,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两个消遣了。”
乔泰赶回后舱,舱门紧闭,里面传出一声痛楚的哀泣。乔泰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玉珠头发,一手持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昏厥过去。
乔泰怒从心起,大吼—声,正要上前擒拿金昌.不留意猛地绊了桌腿,合扑跌地。
金昌嚎叫了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乔泰背脊正待刺下,玉珠跃起一把拖住金昌大腿大声叫:“乔大哥,快逃!”
金昌猛一挥手,匕首刺人了玉珠胸膛。玉珠惨叫了一声:“乔大哥,他们正偷运黄金哩!”
乔泰听了,如霹雳轰顶,站起身子,一手揪住金昌臂膊,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拳,打得金昌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齐流淌,忙又回头抱起玉珠,玉珠已经不省人事,血流满身。嘴里还不住念着“乔大哥”。
乔泰抱起玉珠刚要出后舱来,见马荣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将玉珠身子托上船面时,玉珠已气绝。
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怒放时节,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泰懊恼不已,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脯,热来横流。半晌,乃道:“马荣弟,玉珠小姐林死前说出,金昌一伙正陰谋私运黄金。”
马荣一手托起金昌待欲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一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没了。
乔泰轻问:“马荣弟可曾寻着卜凯那厮。捉住了他,不愁问不出私贩黄金的内情来。”
马荣愤愤道:“不知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
乔泰拭去了泪水:。“我们此刻即命老鸨及船工将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随即回县衙去禀告老爷。”
马荣点头,忽又想到说,“适才我听卜凯说及,这条船的船主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孟平。倘真的是卷入金昌一伙黄金走私,这顾孟平想来也难脱干系。”
两人回到船头,老鸨及众船工早惊惶失措地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
马荣见远远水面上漂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立着卜凯,竟在放声长歌哩,心中好不气恼,恨得牙痒痒,一味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