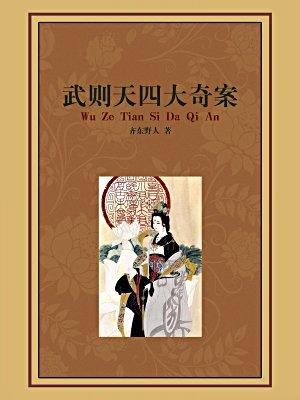紫光寺-第三章
辰牌交 尾,南门里外正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行人如鲫。唯白莲湖一围波光粼粼,青雾淡淡,犹是夙凉未退。一行一行垂柳如一队队齐整的舞姬将飘飘袅袅的长条披拂在水面上,湖中落花墩上的一尖宝塔在碧玉般的湖波中显现出纤细窈窕的身影。
狄公、马荣两人一番乔装,行走在街头,似未被人认出。看看到了南门里最热闹的市廛,马荣忽见一个女子睁大一双眼睛紧紧瞅着他两个。那女子形体颀长,婷婷如玉树,身披道姑的玄袍,头上包裹着大幅羽巾,遮去了半边脸面,只露出那对红丝布满的眼睛,似有一团 怒火放出。
马荣不觉看呆,心中纳罕。路上一顶大轿吆喝横过,那女子倏忽不见了影踪。
“右边折入便是孔庙后街了,那骨董铺就在街心中。”狄公说道。他忽见马荣木然站定路边,神色迷惑。
“马荣,你看见什么了?”
“老爷,有一个女子老远瞅定我们,一对眼睛直欲喷出火来,端的令人生疑。”
狄公四处一望,笑叱道:“休要疑神吓鬼的!恐是你自己见了女子,眼睛喷出火来了。”
马荣待要分辩,见已到了那骨董铺门首。狄公推门而入,柜台后一个面目清癯的老掌柜笑盈盈迎上前来。
“客官可是要为太太办一二件金银首饰,玉器簪镯。”说着手中早已托出一个莹润透剔的碧玉盘,盘内金银钏镯。珍珠项链、耳坠指环烁灼闪光,夺人眼目。——再看柜橱内却都是一些黯淡无光的古旧瓷瓶。宝鼎香炉;墙上一幅幅名人字画,地下一尊尊土偶木雕。——原来这店掌柜还是以鬻卖金银玉器为大宗。
狄公选了一对细琢成梅花枝形状的红玉手镯。——镯上系着一小字片标有价目:二十两银子。
狄公付了银子,笑问道:“掌柜的可记得我?今日一早我已来过贵号,选买了一个紫檀木盒,盒盖上镶有一块白玉的‘寿’字。”
老掌柜眯了眯眼睛,细认了一下,呵呵笑了:“正是,正是,莫非那木盒不称太太意,欲来退回。”
“不,只想打问一下那木盒来历,那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佳构。我收藏时总想注上它的来历,譬如出于哪朝名工巧匠之手。”
老掌柜眨了眨眼,又搔了搔头:“罢,罢,客官还有这等雅兴?这木盒出于哪代名工之手,在下委实不知,只知值钱便收进了。待我去查阅一下账簿,那上面我都清楚记载了出入账目的详备。”说着去银柜抽屉里拣出一本厚厚的簿册,逐页翻阅。
“有了,有了。客官,那紫檀木盒系三个月前从李珂先生手中购得,与一篮破旧古玩一并购进。客官可去找那李珂先生问端绪。”
“李珂是何人?何等营生?”狄公急问。
“嘿嘿,那李珂是一个行止怪癖的丹青手,画得一手好山水哩。可惜命运乖蹇,无人赏识。到如今还蜗居倦曲在一个小破屋里,门可罗雀,鬼都羞于登门。”
“这李珂现居何处?”狄公问。
“他那小破屋便在鼓楼下横街内,肮脏不堪,客官倒有兴味与他交 识?不妨告诉客官,那李珂的胞兄叫李玫的,正经是个家私万贯的阔爷,东城开着爿金银首饰号,清一色的金器、银器、珍珠宝石。敝号比起他来真所谓小巫见了大巫,只一堆旧破烂,值几个钱?客官见了他时,认个朋友,才有意思哩。”
狄公不解道:“李玫既是位阔爷,如何他的兄弟李珂却贫寒落拓。”
老掌柜叹道:“孝悌,孝悌,李珂他最不看重一个‘悌’字,向来不知敬重兄长,行止狂僻,气格乖戾。日子长了,兄弟间自然视同陌路。”
狄公点点头,将玉镯仔细包裹了纳入衣袖,辞谢掌柜走出骨董铺。
“马荣,这里离鼓楼甚近,我们何不乘此去拜访一下那个李珂呢?”
马荣答应,跟随狄公转去鼓楼。
鼓楼后背果有一条横街,在街口狄公问清了门户,很快便找到了李珂居住的那幢破旧不堪的小屋。
狄公在木板门上扣了半日,总算开了,见是一个睡眼惺松、衣衫不整的高个男子。干瘦的脸颊上杂乱地长着几撮黑脏胡 子,一件破旧的长袍上粘满了颜色污斑。
“你们是谁?如何贸然闯来寒舍。”
李珂惊惶地望着狄公、马荣,一对眼睛闪焰不定,满腔疑惧和敌意。
“足下便是李珂先生吗?”狄公揖礼。
李珂木然点了点头。
“县令狄老爷亲驾过访,还不知礼?”马荣忍不住开腔了。
李珂心中一震,畏忌地瞅了狄公一眼,慌忙躬身还礼,一面吐出几个字来:“小人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听说李先生丹青高手,卓有造诣。本县最是喜爱山水字画,今日偶尔路过,顺便拜谒崇阶,以慰渴望。”
李珂尴尬道:“小人雇的帮佣这两日不在,屋里杂乱一片,不堪狄老爷驻息。”
“无妨,无妨。”狄公笑道,一面踱入内房,自往画桌边一把交 椅上坐了,欣赏起桌上的画具来。
笔筒中的笔尖都已干裂,洗子内无滴水,石砚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土。一大幅绢帛摊在桌面上,却搁着腌菜和碗瓢。狄公不由紧蹙双眉,摇头叹息。
墙上的画轴,“山水”不多,秦关汉月,瀚海砂碛,长河驼影,伽蓝风日,大凡高韵神秀,极有风骨。其余皆是佛画,多以佛典故事为题,有的还杂以异教邪神,龇牙咧嘴,形态怪诞。——这兰坊城五胡 杂居,九教并兴,婬祝滥祭盛行。神象圣座,名目繁多,辅以彩施金妆,撩乱人目。——一面观赏,狄公忍不住喟叹频频,心中恼怒。
“李先生是画山水的名手,如何笔下这许多异端邪神,污人眼目。”
李珂眼睛一眨,小声答道:“回复老爷,此地的人,出门便见山水,终岁相厮守者也是山水。这穷山恶水,又有何起解?你再画得形态逼真,为印印泥,谁人赏知?倒是那些佛画卖得出手哩。”
狄公点点头:“本县这就向足下订购一幅中堂大山水,画得佳时,出十两银子,足下意内如何?我再将你遍荐于名贤巨宦、墨人騷客,让他们也来买你的山水。——只一桩,以后再不要画那等异教邪神了,归宗尧舜文武、周公孔孟才是我们的正道。”
李珂不禁跪下,磕头称谢。
“李先生起来,你认识这木盒吗?”狄公从袖中将出那口紫檀木盒,放在桌上,一面细看李珂的脸色。
李珂十分惊讶,心中狐疑:“老爷,这木盒小人从未见过……老爷如何想着要小人验认这木盒来。”
狄公用手拭了拭那方白玉的‘寿’字,只不言语。
李珂平静道:“这种木盒骨董铺里或可买到。漫说小人没钱,即便有钱,也不买它。”
狄公将木盒纳入衣袖,微微一笑,又似漫不经心问道:“令兄长李玫可曾买过你的字画。”
李珂陰沉了脸:“家兄是个经纪人,坐贾行商,只知赚钱,与这笔墨丹青丝毫无缘。又每每轻觑小人,故长久时不曾过往。”
狄公正色道:“本县猜来,足下中馈尚虚,孤身一人幽栖于此。噢,足下适才说雇了一名佣工,相帮料理生计。”
李珂脸上闪过一丝陰霾:“老爷,小人早就设誓,终身不娶,唯以笔墨纸砚为伴。小人那帮佣杨茂德也只是服侍铺纸研墨。裱褙度藏诸杂事,可惜老爷今日没见着他。他手脚伶俐,肚内尚有许多文墨哩。哎哟,惭愧,惭愧,茶水尚未与老爷敬一盅哩。”说着起身寻茶壶。
狄公道:“本县告辞了,此刻正等着我早衙理事哩。拜托的中堂山水,勿忘了便是。”一边站起身来拱手退出内房。
李珂一直送到门口。
转出横街,马荣便骂:“李珂这厮当老爷的面信口扯谎。那老掌柜的账簿上注得清楚,李珂竟不肯承当,花言巧语糊弄。看来这木盒蹊跷,正须在李珂身上问破哩。”
狄公点点头:“此刻我先回县衙,你可在这左右街坊间询问李珂的行止。顺便也问问那个杨茂德的去踪,李珂不是说,他有两日没有回来了。”
马荣答应,心中便打草稿。
狄公走后,马荣四面周围一转,见横街角首摆着个裁缝摊,凉棚下一个五十开外的胖女人正在剪裁一幅素绸。马荣笑吟吟凑上前去:“老人家好生意哩,恁的勤快,又占得方好地皮。”
胖裁缝抬头见马荣装扮,威武十分,不敢怠慢,遂应道:“承客官称奖,可这生意却清淡哩,哪里是好地皮?”
“那边对门里都居住着没婆娘的光棍,这制衣裁帽的,还不是求你。”
胖裁缝鼻孔里嗤了一声:“客官指的莫不是那个画画的穷酸,一个铜钱买饽饽,方孔里还要照几照哩。屁股露在外面招风儿也不肯买一条裤子穿,哪能赚到他的钱?他那个仆人更是个无赖泼皮,狐朋狗友一帮,愉摸嫖赌,哪般不来?这半边街坊都躲他们哩。”
“这李珂的贫困十分,那杨茂德行止邪辟,如何勾搭作一处,成了主仆俩。”马荣疑惑。
女裁缝狡黠一笑:“天知道他两个是如何勾搭作一块的。哼,这半边街坊几番见到那个木板屋,深更半夜有女人进出,这行止如同猪狗一般,真是玷污了这一条横街的名声。那日我都要迁挪别处去了,亏客官还说是好地皮哩。”
马荣听得仔细,讪讪谢过,唱个肥喏,自顾摇摆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