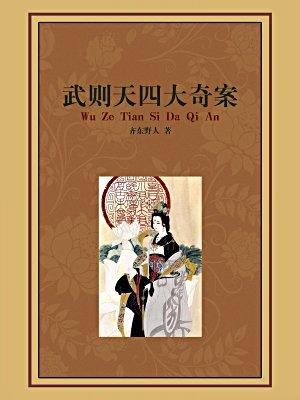第二十回 简勒先智使舅老爷 殷孺人大闹黄知县
却说殷成见了勒先,便道:“老简!我同你赶老羊去。”勒先笑道:“好好!你来的正好!你要赶老羊也可以,只是小了不来!”殷成道:“一百文一注。”勒先道:“太小!”殷成道:“二百。”勒先道:“太小,太小!”殷成道:“三百、四百、五百、一千!”勒先道:“小,小,小!”殷成道:“十两银子!”勒先还是摇头。殷成道:“老简!你在哪里发了财来?我不和你赶羊,你好歹先借几两银子我用!”勒先道:“没得借!要就我们来赌!”殷成道:“你要赌多大才来?”勒先道:“古人有说的,‘一掷千金’,你要依得这个,押下一千两黄金,我就同你赌。”殷成大笑道:“老简!你敢是疯了么?”勒先道:“我不疯,不过你穷点罢了!哪一个随任做了嫡亲舅老爷,象你这种寒酸的!”殷成道:“我也这么想,只是没有个弄钱的路子。”勒先道:“你只要押了一千两金子,做个孤注,我同你赌个输赢,你赢了我的,自然就有银子了。你要知道,一两黄金十六换,这一千两黄金,有一万六千银子呢!”殷成道:“你没得给我呢!”勒先道:“只要你赢得,我没有赖帐的。”说罢,一把拉殷成到自己寓处,取出骰碗道:“来,来,来!”殷成笑道;“就是一千两黄金一注,你要赖了,我叫我姊夫扣住你,不怕你飞上天去。你是头家,快掷快掷!”勒先掷了一把,是个九点。殷成道:“这回赢定了!掷了两把没有。因取起骰子,在手里搓了一搓,用力掷去,那骰子落碗,见了三个二,两个六,还有一个在那里转呢。眼见得转个六出来,便是分相,要赢了。殷成连忙扭住了勒先衣襟,对着骰子喝声:“六呀,六六六!”果然转了个六出来,却把一个二打翻了,变了个四,只得八点,恰恰输了。殷成一撤手,翻身就跑。勒先连忙赶上,一把拉住。殷成着急道:“你剥我的皮!”勒先道:“舅老爷!不要这样,我有句说话和你商量!”殷成道:“没有商量,除了剥我的皮!”勒先捺他坐下道:“舅老爷!请坐,我们不过取笑,谁来认真呢!”殷成道:“认真也不要紧,我有一条命!”勒先笑道:“我拿甚么做胆,敢要舅老爷的命?此刻金子是有一千两在这里,不知你要不要?”殷成道:“你莫非在这里做梦么?”勒先道:“我并不做梦,却是梦也想不到的,这注横财,只要你有本事拿!”殷成这才觉着话里有因,便问道:“是甚么横财?用甚么本事去拿呢?”勒先就把梁天来告凌贵兴一节说了,又道:“凌贵兴实是被他诬告,因此气忿不过,情愿送一千两金子到里面,要伸这个冤。舅老爷如果说得里面收了,还另外谢你一千银子,再有本事说得里面一文不要,岂不是这一千黄的,一千白的,都是你舅老爷的么?”殷成沉吟了一回道:“我且说去,碰碰运气,说得成功时,请你到谷埠去开厅。”勒先道:“多谢舅老爷。只是越快越好!”殷成也不答话,站起来往里就走。一路上暗想到:“我何妨把一千银子许了他,我自己却落了一千金子,岂不是好!”又想道:“不好,不好!太少了!恐怕买他不动,不如许他五百金子吧!”一头想,一头走,不觉走到了签押房来,黄知县正在那里看公事呢。殷成走了进去,叫了一声姊夫!黄知县抬头一看道:“你这几天干甚么事来了,总是十天半个月不见面的。你自己照照镜子看,一脸都是野气,我劝你安静点,在书房里临几行帖,看两篇书吧!就是正经书看不懂,看看小说,也好拿来定定性,何苦成天在外头混,混得个甚么道理出来!”殷成道,“姊夫,你还埋怨我不看书呢!我前回从家乡带来的一部大板金瓶 梅,你又拿来烧了,说是甚么银(谐淫字声)书。你单怕我在银书上看了银子下来发了财,是不是呢?我此刻倒送金子给你,好不好呢?”黄知县道:“你不要和我胡说,里头去吧!”殷成道:“不是胡说,是件真事!就是梁天来告的那个状,那凌贵兴是冤枉的!”说到这里,又想道:“五百金子,还怕买他不动,不如多给点与他吧!我少赚点就是了!”又道:“他此刻托人来说,求姊夫代他伸冤,他情愿送八百两黄金给你用呢。”黄知县大惊,怒喝道:“你在外面胡 混罢了,怎么干预我的词讼起来,你小心点,还不快滚出去!”殷成初意,以为一说必成,谁知碰了一个大钉子,没好气,三步两步走出签押房,到上房而去。
殷孺人正在那里打丫头,骂老妈子,殷成也不理会,一直走到他姊姊床 上,就睡下去哭。孺人打骂了一回,走到房里一看,见了这副情形,大惊道:“兄弟!你做甚么?”问了两声,不见答应。又问道:“可有甚么人欺负了你?快点告诉我,我与你出气!”殷成见问,越发哭得厉害。歇了良久,方才抽咽着说道:“姊……姊姊!你借给我几个盘费,我回江 西去,姊夫撵我呢!”殷孺人听了大惊,猛然叫道:“丫头!请老爷进来!”
不一会,黄知县进来了。殷孺人道:“你要撵连我一齐撵了去,只要你打发盘缠,我姊弟两个,马上就滚!好等你另外拣一个又贤惠,又标致,又和顺,又是娘家人死个精光的,方才娶了来做太太。我却没有这种福气,只好跟着人家在接头研墨,伺候他卖字,卖了百十来个钱,买米烧饭吃,哪里有福气住在衙门里来!本来呀,这是要有福气的太太住的衙门,我们是小人家出身,只配受穷苦,还不自谅,要千山万水走到这里来,受人奚落!兄弟!快点起来!卷铺盖,咱们走,男子汉,大丈夫,哭甚么!你虽然没本事,写出字来卖不出钱,终也不见得就饿死了!咱们放长眼睛,看人家升官发财!”说罢,又一叠连声催卷铺盖道:“就连盘缠也不开发,我讨饭也讨了回去,好歹丢不着我妇人家的脸:”黄知县道:“好端端的闹甚么?我不懂呀!”殷孺人道:“啐!谁要你懂我的事来!我的兄弟不争气,死捱在这里,还够不上一个奴才三小子。我当日文不是明媒正娶的,是个偷跑跟汉子的,我兄弟便是个王八乌龟崽子,所以人家要撵就撵!黄知县怒道:“孺人!你这是甚么话? 他只管在外头混闹, 自己也不顾惜自己的身份……”殷孺人连忙插嘴道:“呸!他本来是个小户人家,乌龟王八崽子,又不是甚么做知县太爷的,顾惜甚么身份么?”知县道:“我也不知呕了多少气,也呕他不好……”殷孺人又插嘴道:“是呀!这个叫做好死的不死,又不见他死了,害得我要说嘴也说不来!”黄知县道:“这也罢了!他今日忽然还要干预词讼起来,难道我说了他两句,就算得撵他了么?也值得这样惊天动地起来!”殷孺人道:“兄弟!怎么你不照照镜子,你是甚等样人,也好去干预人家的公事,怪不得受人家的羞辱,却跑至我这里来哭!”殷成听得,一骨碌爬了起来道:“姊姊!这才是‘狗咬吕洞宾’呢!我常常听见人家说,做了官是用大秤称金子,小秤称银子的,我们这个番禹县,又是有名的好缺,衙门里却是冰清水冷的,外面的人说起来,都说如今这个县官是个呆子,有钱不会用。我听了这话,很是纳闷。我今天出去,遇了一个乡绅人家的师爷,说起什么梁天来诬告了凌贵兴,此刻凌家肯出八百两黄金,送到里面来,求伸这个冤。知道我是舅老爷,专诚来托我的,我又不曾招揽他,谁知姊夫倒要撵起我来!姊姊!一两黄金十六换,这八百两黄金,一八如八,六八四十八,有一万二千八百两银子呢!我一片好心要送万把银子进来,倒受了这个气,你道可恼不可恼呢?”
殷孺人忙问道:“兄弟!怎么说呀!人家就肯拿八百两金子送我们吗?你为甚不来和我说?”殷成道:“和你说便怎么?也要他肯代人家伸这个冤枉,人家才肯送呢,和你说便怎么?难道人家肯白送你么?”殷孺人屈指计道:“八百两,一两黄金四两福,四八三十二,是三千二百两,足足有两担福呢!我们不知有这两担福没有?老爷!你为甚放着送上门的金子都不要?是甚么道理?难道你穷的还不怕么?”黄知县道:“他这个公行贿赂得,我哪里好胡 乱受他?我又没有审过,知道他们谁曲谁直。倘使收了他的,做出那纵盗殃民的事情,便怎样呢?况且我做官,自有做官的廉俸,我不贪那意外之财!”殷孺人道:“呸!不说你没福,说甚么纵盗殃民,你既然说没有审过,哪里就知道是纵盗殃民呢?这是个甚么案情,你说给我听。”黄知县不则声。殷成道:“甚么案情?是一个姓梁的,被强盗打劫了,闹了个七尸八命,那姓梁的不来告强盗,却告了一个姓凌的读书人,说是那姓凌的指使出来。”殷孺人道:“那八百两金子,是哪一个送的?”殷成道:“就是那姓凌的,被他诬告了,所以肯送出来,求姊夫同他伸冤呀!”殷孺人忽的一下翻了脸,对黄知县道:“这等顺水人情,你也不肯做,难道我嫁了你,就应该穷一辈子,不应该享一天福的么?姓梁的所告,既然是个读书人,你怎么就说到纵盗殃民起来?你没有发迹的时候,也是个读书人,难道那时候你也是强盗么?”黄知县跌脚道:“唉!你怎么这样糊涂?他不是告姓凌的做强盗,是告他纠合强盗来打劫伤人呀!”殷孺人道:“我不糊涂,你才糊涂呢!你也是个读书人,你纠合过强盗么?你可曾认识过一个半个强盗么!我只当你读书明理,惺惺惜惺惺,谁知你倒拿同自己一般的人,当做强盗,还说我糊涂呢!”黄知县道:“我何尝就说他定是个强盗!因为不曾审过,哪里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呢!”殷孺人道:“你看!你还是这样糊涂呢!你要疑心到读书人是强盗,你为甚不疑心你自己也是强盗?这件事明明是姓凌的受了冤枉,明天坐堂,先把姓凌的出脱了,然后另外派差去捉强盗,也不亏了姓梁的了。这八百两金子,你不受我就受了!夫妻们好也这一遭,不好也这一遭,好的大家享用,不好的我就拿了它做盘缠,回江 西去,由得你在这里做清官!兄弟!你先出去,叫他把金子即刻兑卞来,包他明天没事,我这里不怕他不依我这个办法!”
殷成巴不得一声,立起来就走。黄知县要阻挡时,哪里还阻挡得住?
不知到底闹个甚么了局?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