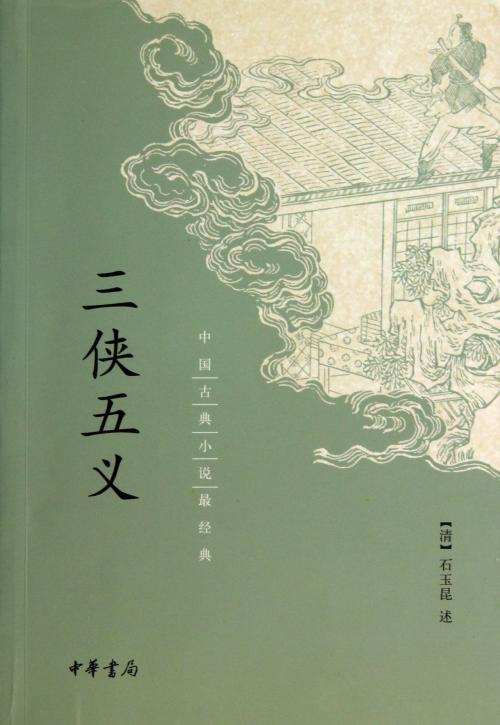第七十六回 降烈马巧遇八郎
孟良叫出野马的名字、说出它的来龙去脉,吓傻了哈密国使者、惊呆了大辽的群臣。人们都纷纷议论:小小渔夫竟有这样本事!
孟良怎么会识宝马呢?原来有人为他帮位二他过河时,张错交给他的那封信,是他舅舅郑道平写的。上次孟良二次归宋,中途巧遇郑道平,曾给孟良一只火葫芦。郑道平见他粗野鲁莽,怕他不学好,就在暗中观察。时过半年,见孟良侠肝义胆,跟随六郎镇守边关,忠心报国,才放心了。他离开边关,找师弟任道安,同去五台山看杨五郎。杨延德见着两位老前辈,很高兴,对他俩说:“近来,北国请了个老道颜容,说要摆座大阵,与大宋一决胜负。”郑道平和任道安一听,都暗暗担心。老哥俩一商量,要去幽州看个究竟。杨五郎说:“我也与你们同行。”就这样,僧道三人到了幽州。住了十多天,他们明查暗访,得知北国已摆下了一座天门阵。偏巧,就在这时,哈密国派使者带着野马,跟大辽赌输赢。杨五郎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怪马,仨人就在驿馆外,待机窥视。这天,他们真看见了。郑道平经多见广,又会相马,他看了后说:“真是匹宝马呀!若武将得了它,那真如虎添翼。只是我们不在其位,与之无关。”任道安听罢,藏了个心眼:若是这样,把它给我徒弟杨景多好呀!他把心事一说,杨五郎高兴,可郑道平说:“怎样才能弄到我们之手?”任道安说:“无妨。我去边关送信,叫他们派人来盗。”郑道平灵机一动:“既是这样,盗马这个功劳,得归我外甥了。”五郎说:“二位老前辈能这样做,我替六弟先谢谢。我也帮不了大忙,孟良进幽州,包在我身上了。”说完分手。
任道安和郑道平两人来到边关,方知杨景有病。郑道平不乐意出头露面,他在暗中等候。任道安进帅府,弄清杨景病源,叫孟良去盗凤发。一切安排妥当后,悄悄告知郑道平。郑老道又找杨五郎,二人同找渔家张错,求他帮忙。张错和杨五郎最好,慷慨应允。郑道平留下一封书信,上边写明马的名字、出产地方,叫孟良揭皇榜、降野马,伺机盗凤发,并把马带回大宋。孟良看信以后,一路上,把信上言词背得滚瓜烂熟,这才去撕皇榜、识野马,镇住殿上的文武官员。
今天要降马,孟良不知道这匹马的性子,心里没底。好在他多年驸马征杀,没少摆弄牲口,况有力气、有胆子,所以他毫无惧色,瞪大眼睛,大喊一声:“我能降!不过,可不能在这降口这马性烈,放出来万一拢不住,你们都活不了啦!”太后说:“对!把它拉到荒郊野外。”肖太后口旨传下来,差人又赶忙把装马的铁笼子装上车,拉到郊外。肖太后由众大臣陪伴和使臣一起来到郊外,到远处一个高坡上嘹望。
孟良抖擞精神,来到铁笼子跟前。一字板肋玉麒麟看见了人,毛都立了起来,隔着栏杆往外直扑。马夫吓坏了,嘱咐孟良:“马要出来咬我,你可得帮忙呀!”说完,战战兢兢地用钥匙打开锁头。还没等把门拉开,这匹马“当!”将门一顶,往外就蹿。孟良在门旁一看,为难了:鞍轿嚼环也没有,没地方抓呀!孟良急中生智,伸手擎住了马的尾巴。这时,野马逞凶了,回头奔孟良“当!”就是一口,吓得孟良踏出挺老远:“好家伙,马还吃人呢!”孟良刚刚躲开,玉麒麟一声咆哮,四蹄蹬开,翻蹄亮掌,跑出去了。孟良不敢怠慢,撒腿就追。野马听见身后有人,心说:这些天可把我憋坏了!今儿个出来散散心,你又要抓我回去?没门儿!跑着跑着,猛地一转身,用头就去撞孟良。这时,大伙都替孟良担心。再看孟良,他先就势仰面往地下一躺,等野马低头咬来时,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抓住马鬓。马鬓挺长,聋拉到马肚子了。他用手一卷,飞身上马。玉麟麟一看有人骑它,更不干了,“唏留”一声暴叫,前蹄腾空而起。孟良还没坐稳呢,被它“啪”一下,扔到马下。周围人吓坏了,估计非摔死不可。孟良不顾疼痛,爬起来要了根套马杆子,连蹄带蹦,又扑向玉麒麟。这回,野马没往外冲。孟良一抖套马杆,“曳”一下,套住马头,用力往怀里一带,就势二次飞身上马。玉麒麟一看:又上来了!它猛一尥蹄子,想把孟良甩下,谁知孟良把马膀子搂住了,两腿夹住马肚子,没摔下去。野马想回头咬孟良,但够不着。这回可把马气坏了:我不走了!它站在那不动弹了。孟良以为马被驯服了,刚要直起身子,突然,那畜牲又发起脾气:先是前蹄子在地上乱刨,然后又四蹄蹬开,象腾云驾雾一样地飞奔而去。孟良合计:你爱往哪去就哪去吧,反正我不下来。这匹马跑得太快了,逢沟越沟、遇涧跳涧,来回穿树、绕石子,不知跑出多远,连气带累,浑身全是汗水了。过了挺大时辰,野马放慢了脚步。孟良见它老实点了,举起锤一般的拳头,照着板肋“当当”就来了几拳,疼得它连声吼叫。紧接着,孟良又打了十几下,这匹马疼趴下了,挥身直哆嗦。这时,孟良从马背上跳下来,来在马头前:“看看咱俩谁厉害?”“当当”又踢两脚。这匹马心说:猛爷呀,别打了,我服了。孟良辨认一丁方向,拉起玉麒麟,飞身上马,往回奔去。等回到原处,肖太后乐坏了:“张高,你是怎么!它降服的呢?”“我一念咒,就把它驯服了。”肖太后这回可气粗了,对哈密国的使臣说:“回去告诉你们国王,以后少生枝节。叫他以后照样给我纳贡,一点都不能少。”“是,是!太后,这匹马是不是由我带回?”“不行!这匹马我扣下了。”“好!就算孝敬太后了。”使臣低头哈腰,匆匆离去。
这时,肖太后乐得拉开了长音:“我说张高呀,你可真有两下子。今后别打鱼了,在朝做官吧!哀家封你——”还等说封什么官呢,孟良忙接茬说:“你别封我,我不爱当官!”孟良心说:我是边关大将、总兵大老爷,要你什么官?肖太后说:“也好!哀家多多赏你金银。”“我不爱财,钱多了招贼。若有图财害命的把我杀了,太后你不就坑了我吗?”肖太后听罢,笑得合不上嘴,更喜欢孟良了:“也罢。这匹玉麒麟我很喜欢,要留哀家乘坐。让你到宫中替我驯马,你可愿意?”孟良一听进宫,高兴了,忙说:“谢太后!不过驯马要出入宫门,不方便!”“这好办。给你一道宫中腰牌,你可随便出入。”说完,把孟良安置在驿馆,把马放在后宫御马棚。
次日,孟良早早就起了床,匆匆吃罢早饭,牵出宝马到大街上溜达,边走边琢磨:怎么能弄来凤发呢?
幽州是北国的军事、文化、贸易中心,又是国都,是中原人、北国人杂居的地方,什么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僧道两门、回汉两教,熙熙攘攘,一派繁华景象。孟良的眼睛不够使了,东张西望。突然,“当当”传来几棒铜锣声。街上一乱,人群往两边闪,迎面跑来二十四匹对子马,后边人打着回避牌,挑着各色大旗,有白道的、红道的、蓝道的……旗后边打着执事,有金瓜饿斧,鹰舞鹰幡,再后边是黄纱罩顶的红轿,轿帘高挑,里边坐着一人:年纪在四十上下,头戴浅蓝色单风帽,上插斗大红缕,身穿蓝绸子大领对襟花袍、内衬白护领,下身拦着看不见。往脸主看:白面黑须、细眉长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孟良纳闷:这个人是什么官呢?打着中原执事,长得也象天朝人,可又是北国的装束。再说,旗上连个姓没有。嗯!我得过去,弄个明白。看!这位愣头青,又来了好奇心。他扬手在马的三叉骨上打了一掌,玉麒麟奔大轿跑过去,冲乱了前边的队伍。差人伸手来拦马头,已经晚了,玉麒麟已冲到八抬大轿前,用头一拱,“当!”大轿倒了,抬轿的八个人全趴下了,那位大人被摔到了轿外。他还算有点功夫,一捉丹田气,站了起来,伸手抓住马组绳,厉声呼喊:“吁!'玉麒麟被带住了。那个人气坏了:“来人!把马夫绑上,打道回府。”本来这位是要上朝的,被这匹马闹得生气了,往回就返。时辰不大,来到一座府门前。下了轿,进大厅,把孟良押进来。
再看那位大人,已换了身中原便衣,坐在正中,问:“你是干什么的?”孟良回答:“马夫。”“给谁看马?”“肖太后。”那人一皱眉,暗想: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呢?”为何去大街遛马?”“幽州城是肖太后的,她的马哪不能去?”“谁让你撞本官的大轿?”“撞轿的是个牲口,怎么你还跟哑巴畜牲呕气呢?”孟良这三言两语,呛得他无言答对。片刻,才又问道:“你叫什么?”“张高。”“从哪来的?”“中原!”那人一惊,屏退左右,又问:“你是怎么从中原来的?”“我本来久在中原占山,近来我爹有病,才回来探望。”“噢!原来如此。”那人打了个唉声:“你到过东京汴梁吗?”“常去。”“可去过天波杨府?”“去过,不就是顺龙大街上无佞侯的府院吗?”“对。现在杨家怎么样?”孟良想:这个人老提杨家干什么?难道他试探我?看他长相,象个中原人,说不定他是投到北国来的。我何不用话敲打敲打,兴许能给我帮点忙。想到这,说:“老杨家世代忠良,京城大人孩子没有不尊敬的。圣上还给杨府修了牌坊、闹龙匾。”那大人又问:“老太君现在身体怎样?”“长寿星可结实了。”“杨门女将呢?”“除了柴郡主,都成寡妇了。唉!说起来也怪可怜的。”他说到这,见那个大人眼圈发红了。孟良更纳闷儿了,忙问:“这位大人,你打听这些干什么?”“本官也是中原人。张高,你怎么对杨家这么熟呢?”孟良说:“我从小在京城跑买卖,离杨府挺近。长大了,又和杨郡马不错。”那大人一惊:“你认识杨六郎?”“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杨六郎现在干什么呢?”“你想知道知道?”“是呀!”“我不说。”“怎么不说?”“你往那一坐,象审贼一样,可我呢?两个膀子都绑麻了。”那人乐了:“是我忘了,多有得罪。”说着,亲解绑绳,又递过座位。待孟良坐定,他又问:“张高,今日遇见你,乃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今天咱俩好好谈谈。”孟良虽然粗鲁,可粗中有细,眼珠一转,有了主意:“大人,你什么时候到北国?”那人说:“十八年前,我和老令公赴双龙会,不幸失身北园。”“您贵姓?”“我乃王顺是也。”
孟良一听,大眼珠一瞪,“腾”一下,站了起来:“这么说你是杨八郎了!”王顺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你是什么人?”“别害怕!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杨郡马的把兄弟、边关大将孟良。我把底都交给你了,快到你老丈母娘那儿请功去吧!”王顺听完,急忙将门关严:“原来是孟将军,失敬了。本官正是八郎杨延!。”
这个愣头青,怎么知道王顺即是八郎呢?这是孟良出边关前,老太君告诉他的。
孟良这张嘴不饶人,挖苦得杨延顺脸面通红,象巴掌打的一样。“孟将军!想当初金沙滩一战,只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洒。可恨奸贼潘仁美,不来解救,我身带重伤,被三公主活擒,求生不得,欲死不可。肖太后要杀,玉镜公主阻挡。她以身相许,要招我为驸马。我想,若不应亲,就得丧命。我就这么死了,杨家仇何人去报?不如卧薪尝胆,暂且应亲,久后逃回中原。成婚后,改名王顺,并和肖太后约法三章:我是中原人,出门或回府,要按中原礼节,我虽是降将,但不能轻看,可以守关,不能交战,尤其不和宋国兵将交锋。我也曾去狼牙寨,给父兄送饭,把关口时,暗中放过六哥、七哥。后来被肖太后发觉,一怒之下,把我软禁起去。从那时起,不让我参与国事,就养在府里。乐意上朝就去,不乐意也没人过问。但有一件,不让出城,怕我偷回中原。唉!十八年来,真如鸟入囚笼、有翅难飞。每到深夜星斗出全,只可遥望南方,仰天自叹!”说到这,他眼圈发红。
孟良说:“你在幽州,享受荣华富贵、妻财子禄,怎么还想中原?”“人常说‘越鸟思南’。禽兽尚有思乡之心,何况人乎?”孟良说:“你一说,我一听,也不知是真是假。要真没忘你是中原人、杨门后,我有个事,你帮帮忙吧!”“理应报恩。”“六哥杨景和宰相寇准,叫王强害了。如今昏昏迷迷,人事不知,老盟娘和嫂子们快要哭死了。多亏任道安看病,开了药方。药引子就是肖太后头顶心的红发,三根就行。我来幽州,举目无亲,找个帮忙的都没有。正犯愁呢,偏巧大街上遇见你了,设法帮忙吧!”
八郎听完,很受感动:盟兄弟都能舍死忘生,来幽州盗发,我虽和六哥不是一母同胞,可从小是老太君拉扯大的。“知恩报德方君子,恩将仇报是小人”,可要弄肖太后的头发,真是比登天还难。想到这里,他遥摇头。孟良一看,着急了:“不给办呀?”“孟将军,不是我推脱。你不知道,算卦人对肖太后说过,因为红发主贵,她才当上女皇上,凤发要剪了,皇位就丢了。所以她当命根子看着!好吧,我慢慢寻机盗发!”“啊?不能慢,拖过七天,盗回去也没用,今天是第四天了,你还得快些。”八郎一听,也着急了,想了想说:“这么办,天黑后你来一趟,听个信。”“一言为定。”孟良走了。
送走孟良,八郎在大厅里急得直转。过了好大一阵,突然眼睛一亮,有了主意。他忙回到书房,往床上一倒,乱喊乱叫起来:“哎哟,哎哟!”书童一看,吓坏了:“驸马爷,您怎么了?”“我得暴病了,速去请公主。”
时辰不大,玉镜来了。这夫妻俩感情挺好,听说丈夫病了,她可急坏了。到床前一看,见杨八郎正在床前折腾呢。“驸马,怎么了?”“公主呀,我活不了啦!快给我准备后事吧。”公主吓坏了:“驸马,何出此言?”“公主呀,这病治不好啦!我从小投军到兵营,不知怎么,就得了这心疼的病。那时,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先生给我调治,才算得救了。谁知今天又犯了,非死不可。公主呀!我死后,你别过分悲伤,叫太后给你另择佳婿,把咱的孩子带大,我就死也暝目了。”说完,泪如雨下。玉镜见丈夫哭得如此伤心,更悲痛万分:“驸马!你我成亲,相亲相爱。想什么法,我也得把病给你治好。待我去找御医。”“不用找大夫,我还有药呢!”“快吃下去吧。”“没药引子,光吃药不顶事。”“什么药引子?”“问也没用,你弄不来。”“你说吧,就是钻冰取火我也给你弄去。”“需要龙须或风发,有一样就行。”“什么叫龙须、凤发呢?”“男皇上的黑胡须,女皇上的红头发。上次老令公用的是八王的龙须。”“哎!我娘有七根红发。”“是吗?”刚说到此,公主又为难了:“我娘不会给呀!”杨八郎见公主犹豫不决,又哼哼上了,比方才声音还大:“哎哟!”猛一翻身,从床上滚到了地下。玉镜真没法了,“驸马,你等等,我找皇娘要去。”她叫宫女伺候着八郎,自己离驸马府急奔皇宫。
驸马府和皇宫紧挨着,是东西院之分。公主过了月亮门,直奔太后寝宫。
肖太后正坐在绢帐里照镜子呢,玉镜没用报信,就闯了进来,紧走几步,跪在肖太后跟前:“皇娘,救命吧!”肖太后吓坏士,急忙下了龙床:“皇儿你怎么了?”“驸马得了暴病,心疼难忍,不行了!”“孩子,快找御医调治。”“他说用不着,只有皇娘的红发做药引子,才能治好。”肖太后一听,眼珠子转了个圈,心说:道人曾说我当北国女皇,就仗着七根红发,莫非这丫头和王顺是要冲我的洪福?想到此,厉声说道:“奴才,那王顺是中原人,你可是我的女儿。把我的红发拔掉,难道你们要谋我的江山?”“皇娘,孩儿不敢骗您,驸马是真病了。”“不行!”“皇娘,看在女儿面上,给几根吧!”“再多言,要你的命。”玉镜见状,不哀告了:“哼!驸马就知道你准不给,不让我求你,今日一见,果然老娘不念母女情。王顺一死,我也不能独生。不如我先死,我们夫妻到陰曹团聚。”说完,取过墙上的宝剑,就要抹脖子。肖太后见女儿要自杀,害怕了:“得了,得了!我看看去。驸马要真病了,别说红发,就是要我的心肝,我也给他;要是假的,我先把他杀了。”说罢,肖太后坐凤辇,来到驸马府。
玉镜走后,八郎歇了一会儿。正在床上等回信呢,外边有人喊:“太后驾到!”八郎听了,连忙又折腾起来。在床上滚来滚去,哼咳不止。太后进来没说话,在床边一站,看了半天,突然,哼哼一阵冷笑:“胆大王顺!你真是班门弄斧,竟敢在老娘眼前装疯卖傻。来人哪,把他从床上给我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