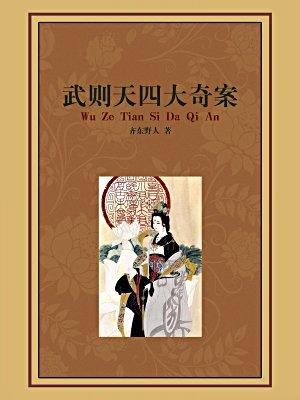第十七则 忍心长舌
林振龙有女曰贤娘,嫁刘公喜为妻,十有一年矣。生一子一翁姑无恙,庐舍晏然。公喜以贸易为生,家虽贫,亦不至馁毙。
公喜父国奕,以坟山雀角,待讯揭阳。适病剧,公喜母携孙往视之,林氏及幼女阿进在家。未几,振龙令归宁以去。邻人以为常事,弗疑也。
及公喜归自厦门,入其室不见其妻。邻人陈孙典,以归宁告。公喜之振龙家,则振龙不见。见妻母钟氏,问贤娘,钟故为骇愕曰:“无之。”公喜言:“某日来在汝家,邻里众目共见,何言无有?”钟氏曰:“固无有也。”
公喜归,沿乡访问,侦为钟氏遣子林开乔及贩者郭阿连嫁卖。以告其族人刘文实,文实率刘国定、刘国重、刘勤、刘连等,偕公喜至振龙家,大噪。振龙父子不敢出。公喜计无所施,将林园所种薯芋残毁狼藉。钟氏出阻,文实等哗然诟詈之。公喜痛妻不见,狂跳叫骂,尤无礼。钟度无退敌之策,入持剃发刀出,当众自划颔颏,诸刘皆惊走。然钟氏刎未及喉,刀伤甚轻,固晏然无恙也。
公喜犹不已,必欲追究贤娘踪迹,来告林振龙卖灭其妻。
振龙亦告公喜卖灭其女。公喜告钟氏谋贩郭阿连,嫁鬻贤娘及阿进,不知所之,索妻女二命。振龙亦告公喜谋贩郭阿连,嫁鬻贤娘及盗薯行凶,杀伤夫妻两命。遣役访摄郭阿连未至,未讯也。越二十余日,钟氏以病死。振龙视为奇货可居,以活杀妻命来告。云钟氏怪刘公喜卖女,公喜听监生刘文进主谋,聚众行凶,逼杀钟氏。而告词后开列元凶,则又系刘文实而非公喜。
拐卖逼杀,皆云文实之事。余见其前后矛盾,不问可知为荒唐。
然事涉命案,不得不为诣验也。
钟年五十有六,旧划刀痕已经全愈。遍身黄瘦,并无微伤。
活杀之控虚诞极矣。但贤娘踪迹未明,黑自难分,势不能以中止。拘出郭阿连问讯,则钟氏前后商谋嫁女情事及遣子林开齐同送贤娘,由惠来而之甲子所,嫁与李姓者为妻,言之历历,皆有确据。而振龙恃有亲属为惠潮观察使心腹干差,专在外访求官司得失,而其族又新近与邑中仕宦者联宗,纪纲数辈罗列尸场,自觉有赫赫之势,坚不输服。
余移檄海丰,并遣隶役偕郭阿连之甲子所,窥伺李家住处,获出林贤娘。交 署尉张东海,遣解来潮。林振龙要贤娘于路,附耳数言而去。
贤娘至,言十八于归,今行年二十有九。生一男一女,男为夫公喜所卖,女为郭阿连所卖。问:“卖汝者谁也?”曰:“刘文实也。”问:“汝与文实有私乎?”曰:“无之。”“无则曷为从之奔?”曰:“为文实之母马氏所欺也。因夫公喜非翁姑所生,被逐,无房舍可居,在文实家借宿。而夫赌荡作贼,不顾妻子无衣无食,遂为文实所卖。”问:“汝父母知乎?”曰:“不知也。”“然则汝自愿嫁乎?”曰:“不愿也。”余曰:“噫!
奇哉!汝二月二十八日在母家,遣嫁何云文实?”曰:“马氏遣郭阿连到我母家绐去耳。彼言翁姑死,令我之揭阳治丧,我是以从之去。”问:“是夕宿何家?”曰:“宿洋内乡郭阿连家,次日宿惠来,又次日宿甲子所。至三月初七日,嫁与李云义,聘金三两,刘文实、郭阿连分之而去。”问:“汝平素与阿连有私乎?”曰:“无也。平素并不识阿连,因马氏遣来始见面,尚诈名阿顺,后乃知之。”
郭阿连以首抢地,大呼曰:“冤哉!我实受钟氏之托,称贤娘新寡,近地婚姻富者非偶,贫者无所得食。惟海丰、甲子多鱼盐之利,易以谋生,人多温 饱。令我同林开乔一行耳。我乃男子,贤娘少妇 ,非亲兄林开乔同行,钟氏肯令其女从我去?
即贤娘亦安肯从素不相识之男人,过都越邑之他郡以去?此理甚明,情甚确。如彼所言,我不服也。”
再讯贤狼,贤娘以父兄先入之言为主,不实供,刑之不变。
讯林开乔,开乔无可答,亦但诿为文实,刑之不变。讯刘文实,文实固称无有。贤娘、开乔力指之,刑亦不变。再讯郭阿连,阿连称止有林开乔母子,与他人无一毫干涉,刑之终不变。
余复呼文实讯之,文实呼天扑地言:“公喜乃我从兄之子,世岂有欺诳侄妇转卖他人之人?且我非游手穷饿,有妻有子,有田有宅,肯作丧心病狂之事,与郭阿连分三两污秽之财?我若果有此情,郭阿连岂甘代罪?刘公喜岂不我怨?即林振龙,焉肯舍我而告为公喜所卖,我又安敢与刘公喜往噪振龙之家,以此嫁祸。有死不服!”
马氏曰:“我二十孀居,苦守二子,今行年七十,足不履户庭,非礼之言不出诸口,岂有劝人改嫁作伤风败俗之事?若有此举,则从前守节皆虚矣。此妇人忍心害理,十余年结发恩深,甘反面从他人以去,又敢诬夫非翁姑所生,又诬以赌荡作贼。宅舍坚好,诬以无室;男子在家,诬以鬻卖。如此妇人,何事不可出诸口,尚以其言为可信乎?”
固遍询邻居陈孙典,房族刘绍万、刘国来、刘文忠,乡保杨鼎显。则公喜素守分循良,无此匪丑行。贸易为生,亦无赌博 。室庐完固。与刘文实尚隔一村,亦无卖子。
乃再呼贤娘问之曰:“汝言公喜卖汝男,有诸否?”曰:“然也。”“卖与谁?”曰:“卖与阿翁刘国奕。”国奕哭曰:“天乎!公喜乃我夫妇亲生之子,公喜之男,乃我之孙,何买卖之云哉?”
余不禁怒发冲冠,命批贤娘颊二十,拶其指,拷之三十,贤娘声色不动。余曰:“野哉!伤风败化至此妇极矣!吾早知其妄,但林振龙挟上司威势,不得不俾尽其词,此妇岂为人所欺者?既明知洋内乡为郭阿连之家,又惠来、甲子日日止宿之处,条分缕析,岂有被欺揭阳之理?且诬夫为赌、为盗,为非翁姑所生,为无室无食。如此泼妇,何言不可出诸口?彼以刘姓为仇雠,为土芥,岂肯为文实所卖?况且登车就鬻,实出林振龙之家,与文实迥然风马。非郭阿连平昔私通,则林开乔之行无疑也。”
贤娘乃服辜,言:“并非与阿连有苟合,但连年饥馑,卖女者多,不止吾父母。”而林振龙、林开乔亦自知不可掩讳,俯首服罪,不敢复诿为文实。但乞免追财礼,欲与刘公喜索殡殓之资。而公喜欲令其赎还幼女阿进。郭阿连言阿进乃开乔、贤娘鬻在甲子所。亦知其处。命赎还之。
问公喜、国奕尚收回此妇与否?父子皆叩头流血曰:“不敢也。”乃听归后夫,即日出境,免使久留是邦,为潮邑山川之玷。郭阿连按律枷杖,林开乔以母丧,故开一面之网。追聘礼,贫无可偿。劝刘公喜姑置之,勿以污秽之财,差及阿堵,使觇门第者,以为有不祥之气。而林振龙以年老姑宽,勿谓有人于宪司之侧,果炀灶藉丛者之泰山可恃也。
译文林振龙有个女儿,名叫贤娘。嫁给刘公喜为妻,已经有十一年了。他们生下一儿一女,家中平安无事。刘公喜以做买卖为生,家里虽然贫寒,但也不至于冻饿而死。
刘公喜的父亲叫刘国奕,因为坟地和人打官司,在揭阳县候审。适逢他病重,刘公喜母亲带着孙子前往探视,林贤娘及幼女阿进在家。没过多久,林振龙让女儿回娘家探亲。邻居们觉得闺女回娘家是平常事,谁也没注意,没有什么怀疑。
等到刘公喜从厦门经商回到家中,才发现妻子不在。邻居陈孙典告诉他,林贤娘回娘家去了。刘公喜赶到林振龙家,林振龙不在。他见到丈母娘钟氏,便问贤娘在不在。钟氏故作惊愕地说:“没有啊!”刘公喜说:“贤娘那天来到你家,邻居很多人都看见了,怎么说没有呢?”钟氏说:“本来就没有啊!”
公喜怅然而回,沿途打听,得知贤娘被钟氏派他儿子林开乔及小贩郭阿连卖嫁了。刘公喜把这事告诉本家刘文实。刘文实率领刘国定、刘国重、刘勤、刘连等,和刘公喜一齐来到林振龙家大闹大吵。振龙父子不敢出来,公喜没有办法,将林家田里所种薯芋弄得乱七八糟。钟氏出来阻拦,文实等一片哗然,叫骂不已。刘公喜因见不到妻子而恼火,狂跳叫骂,尤为无礼。
钟氏一时想不出办法,转身进屋提起一把剃头刀子,当众自己划破下颏。刘家一群人皆惊走。其实,钟氏并没割到喉咙,刀伤很轻,所以安然无恙。
刘公喜还不肯就此了结,一定要追究林贤娘下落,就来至县衙状告林振龙拐卖其妻。林振龙也来状告刘公喜拐卖其女。
刘公喜告钟氏与小贩郭阿连串通,拐卖贤娘及阿进,妻女下落不明,定要索回二人。林振龙告刘公喜串通郭阿连,拐卖贤娘,并糟蹋番薯,在地里行凶,杀伤夫妻两条人命。我于是派遣差人寻访捉拿郭阿连,但一直没有捉到,所以也就未能审讯。
过了二十多天,钟氏病死。林振龙这下子可抓到把柄了,把妻子的死当作奇货可居,状告刘公喜活杀人命,说是钟氏责怪刘公喜拐买女儿,刘公喜听信本家监生刘文实主谋,聚众行凶,逼死钟氏。但告词后开列的元凶则又不是刘公喜,而是刘文实。称拐卖逼杀,都是刘文实干的。我见状子前后矛盾,不问可知荒唐已极。然而事关人命,不得不前去检验一番。
钟氏五十六岁,下巴上的刀伤已经全好了。身体黄瘦,全身没有一点伤痕,所谓活杀的控告显然荒诞之极。但考虑到林贤娘下落不明,黑白难分,所以还不能就此结案,便将郭阿连拘捕来审问。郭把钟氏怎样串通他商量女儿改嫁,怎样派遣儿子林开乔和他一起送走贤娘,怎样从惠来到甲子城,将烯娘嫁给李家为妻,统统交代出来,说得有根有据。但林振龙仗着自己有个亲属是惠潮道台的心腹干差,专门在外访求官吏表现,而他的家族新近又和当地的官宦人家联宗续谱,官宦人家的奴仆不少人来到现场,便自觉有权有势,怎么也不肯认输。
我向海丰发出公文,并派公差和郭阿连一起到甲子城,暗中侦察李家住处,找来林贤娘,交 与署尉张东海,押解到潮阳来。林振龙在路上拦住贤娘,悄悄地咬耳朵,叮嘱了几句话便离去了。
林贤娘来到县堂说,她十八岁出嫁,今年已经二十九岁,生下一儿一女。儿子被丈夫公喜卖掉,女儿被郭阿连卖掉。我问:“是谁将你拐卖的?”她说:“是刘文实。”我问:“你与刘文实有私情吗?”她说:“没有。”我又问:“既然没有私情,为什么跟他一起走?”她说:“是受了刘文实的母亲马氏的欺骗。因为我丈夫刘公喜不是公婆亲生,被赶了出来,没有房舍可住,便在刘文实家借宿。而丈夫刘公喜吃喝嫖赌作强盗,也不管妻子孩儿衣食有无,于是被刘文实所卖。”我问:“你父母是否知道此事?”她回微:“不知道。”我又问:“那么你自己愿意改嫁吗?”她说:“不愿意。”我说:“噫!这事可就奇怪了!你二月十八在娘家被嫁卖,怎么能说是文实送你改嫁的呢?”她说:“马氏派郭阿连到我娘家骗去的。他说我公婆死了,让我到揭阳治丧,我所以跟他去了。”我问:“这天夜里住在谁家?”她说:“住在洋内乡郭阿连家。第二天住在惠来,第三天住甲子城。到三月初七那天,我嫁给李云义,聘金是三两银子,刘文实、郭阿连两人平分而去。”我问:“你平日与郭阿连有私情吗?”她说:“没有。过去并不认识郭阿连,因马氏派他来我娘家才见面。开始他还假称阿顺,后来才知道真名。”
郭阿连听她这番招供,以头撞地,大声呼叫道:“冤枉啊!我确实是受钟氏之托。钟氏说贤娘新寡,想要另嫁。近处嫁给富人家不般配,嫁给穷人家吃不饱肚子。只有海丰、甲子城一带是鱼米之乡,还出产食盐,容易谋生,人多温 饱,让我同他儿子林开乔跑一趟。我是男子汉,林贤娘是个少妇 ,如果不是有亲兄弟林开乔同路,钟氏怎肯让她女儿跟着我去?就是贤娘本人,怎肯跟着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穿城过县到外乡去呢?这道理显而易见,事实清清楚楚。像她刚才所说,我不服气。”
再审讯林贤娘,林贤娘听信她父兄预先交代的话,不肯如实招供,上刑也不改口。审讯林开乔,林开乔无言以对,只是全推到刘文实身上,上刑也不改口。审讯刘文实,文实根本否认。尽管林贤娘、林开乔极力咬住他,上刑他也不改口。再审讯郭阿连,郭阿连说此事只与林开乔母子相关,与其他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受刑终不改口。
我重提刘文实复审。刘文实呼天撞地,说道:“公喜是我堂兄的儿子,世间岂有拐骗侄媳转卖他人的吗?况且我并非游手好闲、穷困潦倒,有妻有子,有田有宅,怎肯做这丧心病狂之事,与郭阿连分那三两银子,图那点污秽之财?如果我真有这事,郭阿连怎么肯代我认罪?刘公害难道不恨我?就是林振龙,怎肯丢下我而告刘公喜拐卖?我又怎敢和刘公喜一起到林振龙家大吵大闹?像这样嫁祸于人,我至死不服!”
马氏说:“我从二十岁就守寡,苦守两个儿子,如今已经七十岁,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到,非礼不言,非礼不动,怎么会劝人改嫁做伤风败俗之事?若有这种事,那么从前守寡守节全都是假的了。林贤娘这个妇道人家伤天害理,不顾十多年结发夫妻的深厚情意,甘心翻脸改嫁他人,又竟敢公然诬蔑丈夫不是公婆亲生,吃喝嫖赌作强盗。明明家里房舍坚好,却说没有住室;明明儿子在家,却说被卖掉。这样的女人,什么话不敢说?什么谣不敢造?难道还能把她的话当真吗?”
于是,我遍问邻居陈孙典,本家刘绍万、刘国来、刘文忠,保长杨鼎显。大家都说刘公喜一向安分守己,善良忠厚,从未有这种不正当的丑行。他靠做小买卖为生,不曾赌博 ,家中房舍坚固完好。他和刘文实隔村而住,从未卖过孩子。
再提林贤娘审问,我问她:“你说刘公喜卖了你的儿子,有此事吗?”她说:“有此事。”“卖给谁了?”她回答说:“卖给公公刘国奕了。”刘国奕听到这话,哭着说:“天啊!公喜是我夫妻亲生之子,公喜的儿子,是我的孙子,怎么谈得上买卖呢?”
我不禁怒发冲冠,命人抽了贤娘二十个嘴巴,拶上她的手指,打了三十大板,而她居然不动声色。我怒道:“好野蛮啊!这个女人伤风败俗到这样,真是达极点了!我早就知道你弄虚作假,但你爹林振龙依仗上司权势,所以才不得不让他把话说完。像你这样的泼妇,难道能被人欺负吗?你既然明明知道洋内乡是郭阿连的家,惠来、甲子城是天天住宿之处,一桩一件清清楚楚,岂有被骗到揭阳的道理,而且你还诬蔑丈夫是赌徒、强盗,不是爹娘亲生,说家里没住的,没吃的。像你这样的泼妇,什么话说不出来?你把刘家视为仇敌、草芥,岂肯被刘文实嫁卖?况且你上车被卖,是从你娘家林振龙那里出去的,与刘文实根本沾不上边儿。如果不是你和郭阿连平日私通,肯定就是林开乔和你一路同行了。”
到这时候,林贤娘才服罪说:“并非我和郭阿连有私情;但连年饥荒,卖儿卖女的人很多,不只我的父母。”林振龙、林开乔也自知再也掩饰不下去了,于是低头认罪,不敢再推给刘文实。但他们请求免于追要财礼,还想向刘公喜索要殡殓费用。而刘公喜想让对方赎还幼女阿进。郭阿连说:“阿进被林开乔、林贤娘卖在甲子城了,他们知道卖处。”我命他们将阿进赎还。
我问刘公喜、刘国奕,是否还想收回这个女人?父子俩都连忙叩头发誓:“可不敢要了!”我便判她归后夫,让她即日离开这里,免得长久留在这块地方,玷污了潮阳的山水。按照律条,给郭阿连带上枷,打了一顿板子。林开乔因母亲去世,即网开一面,予以免刑。向林家追回聘礼的问题,因林家贫困无力偿还,我就劝刘公喜且把此事放到一边,不再要林家偿还那污秽钱财,脏了眼睛,玷污了门第,带来不祥的晦气。林振龙未给刑罚惩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在道台大人身边有人,就真的有泰山作依靠,可以借火取暖、借树乘凉,而是因他年老姑且宽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