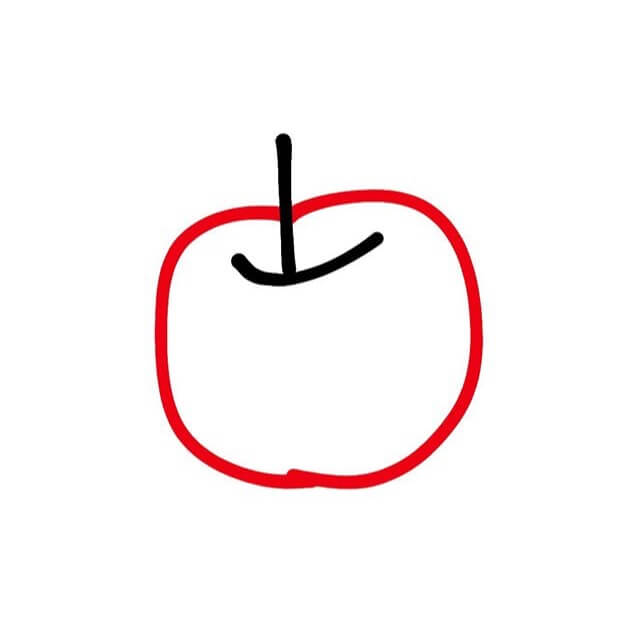春江水暖
春天的消息,藏在一条河里。它的声音很微弱,岸边一排细细的泥沙就能把它挡住,但它的声音偏偏能传得很远,跨越炊烟和工厂的粉尘,直飘到高楼上,沿着耳廓的弧度荡进梦的夹层。于是人突然兴起了念头,春江水已暖了吧?
当人意识到春天到来的时候,春天已经为自己做了双漂亮的草鞋,从河的那边走到了这边。把冰层踩碎,把积雪踩化,脚步一顿,便有一个水泡泡悄悄推开一圈圈的涟漪。
一条河苏醒了,春天才能度过“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铺垫,进入草长莺飞的副歌。
你听,河水寂寞的诗行已押上中华田园鸭活泼的韵脚。它们虽然一身杂色羽毛,没有拿捏得恰到好处的高贵气质,也没有优雅而修长的美颈,但其最是与河水亲近,时不时就钻进水中“串门”,再顶着一片水花钻出来,与水打成一片。水中岸上,湖面河底,水所能讲出的波光粼粼的俚语它都了然于心,嘎嘎的叫声是热情的应和,把一年之计的家常慢慢拉开。
难怪有人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怎么肯迟到呢?鸭子是最自由的,也是最急不可耐的。为了用喙衔起水中的落花,写上一首芳菲缠绵的情诗,刚等到冰雪消融,它们就抢先冲了进去。哪怕水还没有暖,但脚蹼划破初春的沉静时,也会让阳光中丝丝缕缕的暖意漏入水中。
那哗哗波动的声音,挠痒了春江的心脏。鱼儿听见了,虾米听见了,水草听见了,甚至连河底最呆笨的石头也听见了。于是从河床开始,一些绿意开始晕染,一些气泡开始奔流,一曲浮于水面的弦乐变得丰富,春天最先在河中变得热烈。因此,我愿把鸭子唤作春江的使者。
此时的岸边,草木初醒,炊烟都有些睡眼惺忪。但隐隐地,已能听见地面之下的狂欢。
这应当是从一截根须喜悦的颤抖开始。它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翘首以盼了一个冬天,看不见日出日落,无法掐算时间,可怜的根须只能根据土壤细微的温度差来判断昼夜的更替,为春天倒数。终于有一天,水开始流动,虽然还带着冬日的清寒,但那一丝丝的鲜活和甘甜,依旧让长久闷在枯寂与沉闷里的根须喜上眉梢——它急急忙忙地将这份喜讯通知了所有的根须,并向上传送到了树梢,“可以生根、可以发芽了”。四季又将开始以绿意为主题的生生不息的轮回,每一条根须都不能缺席。
渐渐地,枝头有了绿色,河水里的浮光跃金也闪烁在树叶之间。我想,春天是随着水一起被根运到了地上的。
当然,这运输的桥梁也包括姗姗来迟的垂柳。它的青丝越梳越长,河水的情思越流越深。随着一条柳枝探入河中,天光云影载着的思念便沿着它被虹吸到树干上。无需朝雨浥轻尘,水畔烟柳自能显出明亮的新色,待到长发及腰,它的脚边就会有鸭子戏水、老牛潜泳,各占一个声部,与桃李对歌。
那么,究竟是鸭先知,还是草木先知春江水暖呢?又或许,是人先知。毕竟这一切都需要人的眼睛去见证,需要一颗等待春天已久的心灵去审美。
河水流动了,生活便也要开始流动了,这是春天给人们的暗示。让想象力与创造力随着水花一起绽放,让坚韧的目光和柔软的心灵与江水一起回暖,把春天的定义从季节延展成对新一年开拓与成长的形容,彼时春天的旋律才真正进入高潮的抒情。